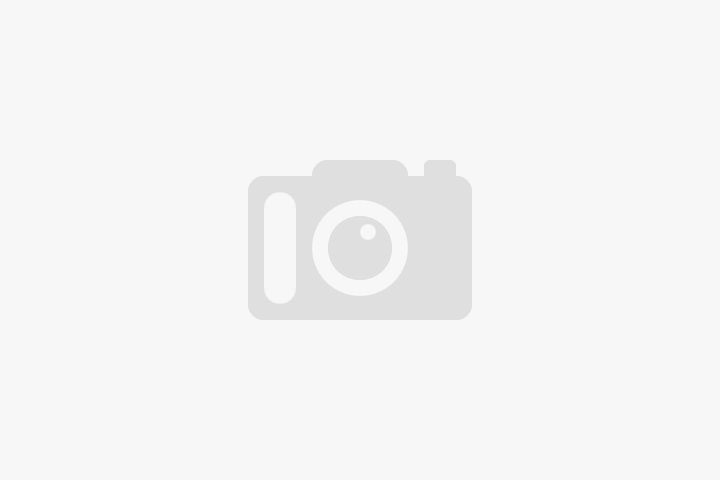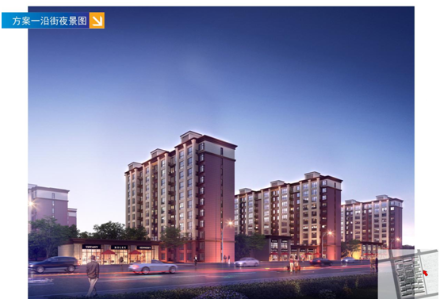微信掃一掃

科爾沁草原的歷史故事
《蒙古秘史》把科爾沁譯為“弓箭手”。成吉思汗稱帝前,曾將其帳殿護衛(弓箭手)編為“科兒沁”,由其弟哈布圖哈薩兒親自指揮。因此“科兒沁”在蒙元之初也是蒙古軍事機構的名稱。現今的科爾沁名稱正式起自蒙元時期,具有“弓箭手”、“神箭射手”之意,作為地名,也可以理解為“射雕英雄的故鄉”、“神箭手的故鄉”。
科爾沁草原,從上古到春秋前期,科爾沁草原上居住的是以講“通古斯”,(也有寫作“突古斯”)語的來自蒙古高原蒙古利亞種系的部族和來自貝加爾湖、西伯利亞以及內外興安嶺之間的游牧民族、漁獵民族和狩獵民族等多個部落群體。這里先后出現了葷粥(音,勛育)、北部、犭嚴狁(音,險允)東部、害夫(音,胡)中部,戎中部、南部,狄南部和中西部等多個氏族和部落,經過長期的戰爭、兼并、交往、融合,戰國至秦漢時期,上述各氏族和部落逐漸匯集成較大的部落聯盟,被稱之為“東胡人”。戰國和先秦時期,這里已形成了以“東胡人”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體的部落聯盟國家,并創造了輝煌的“東胡文化”。繼之以后的則是烏桓和鮮卑活躍在科爾沁草原之上。
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,凡是能入主中原建立長期封建政權的少數民族,都是來自東北亞的少數民族(西北民族則很少),而且這些民族的幼年時期都是在蒙古高原或貝加爾湖、西伯利亞遠東一帶渡過,他們一旦游牧翻過大興安嶺進入了松遼平原之后,馬上就會迅速強大起來,只要有100-200年的相對安寧時期,他們就會成長壯大。然后以其新生的勃勃生機越過燕山山脈,進入華北平原,完成封建化過程。著名歷史學大師翦伯贊先生在《內蒙訪古》一文中說:“假如整個內蒙古是游牧民族的歷史舞臺,那么這個草原(按:指呼倫貝爾草原)就是這個歷史舞臺的后臺,很多游牧民族都是在呼倫貝爾草原打扮好了,或者說在這個草原里裝備好了,然后才走出馬門”。然而任何一個漁獵游牧民族一旦進入自然條件較好、地理條件十分優越的科爾沁草原,就會快速成長壯大,為不久的將來進入中原打下良好的基礎。這是因為北方游牧民族未進入科爾沁草原之前,大都生活在蒙古高原和興安嶺以北的地域,那里四季變化明顯,自然條件相對惡劣,嚴酷的自然環境,將生活在那里的游牧民族進行了嚴格的自然淘汰,這使只有身體強健,抗御自然風險最強的個體得以生存下來,并逐漸使部落群體中每個個體都是最優秀、最強健者。游牧狩獵過程中只有群體相互配合才能獲得生存的最大空間,這就客觀上促成了每個游牧或狩獵部落都有著較強的組織性、紀律性,在協調有序的生活規律中生活。漠北和嶺北地域空間廣大,但生態環境和生存氣候較差,無霜期短、寒冷周期過長,這對原始畜牧和原始狩獵活動都造成了較大的影響,特別是對游牧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繁衍都造成嚴重障礙。可是當她們一旦翻越興安嶺進入廣袤的科爾沁草原,這里宜人的氣候,廣闊平坦、水草豐美的草原,使他們具有的優勢得以迅速發揚,象雄鷹飛入了藍天,象駿馬奔馳進了草原,是科爾沁草原將她們養育得人強馬壯,為入主中原做好了充分準備。
科爾沁草原,讀過浩繁的中華歷史,人們常說“關東出相,關西出將,江南出才子”。
?
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物,深沉厚重的中原文化,必然培養出一批遠見深謀的治世奇才。滔滔不息的黃河之水,溝壑縱橫的黃天厚土,造就一批性格堅毅、勇猛威武、能征貫戰的猛將。鐘靈神秀的江南山水,派生出來的肯定是飄逸俊秀的文人高士。那么科爾沁草原的昊昊高天、茫茫草原、蒼莽雄渾的崇山峻嶺,粗獷豪放的民風又養育出什么呢?北方草原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博大。這種博大的自然環境,孕育出的必然是中華民族最驕傲的子孫,必然是胸懷寬廣、吞吐四海的大英雄。他們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開疆拓土,立馬揚威,為整個民族進步做出了極大的貢獻,為中華民族的強盛立下了不朽的豐功。科爾沁草原這方水土出“天之嬌子”、出大英雄,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草原英雄,他們演繹了無數驚天動地的故事,他們書寫了震驚世界的人類文明的歷史!
-

富源豪庭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華府在售
科左后旗 33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寶典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恒益·悅城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清華里在售
科左后旗 33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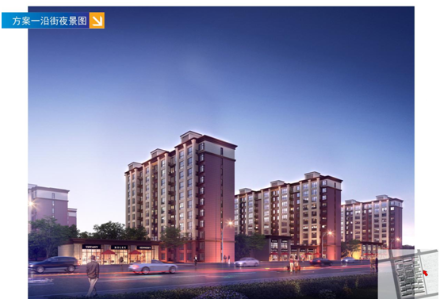
逸品藍山Ⅱ期在售
科左后旗 31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怡景嘉園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福園(理想家園B區)在售
科左后旗 30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郡府在售
科左后旗 3935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富源龍庭待售
科左后旗 409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博王·昊龍公館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甘旗卡商業廣場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
-

團結東區
科左后旗130㎡| 6室2廳 0元 面議 -
溫州商城二樓精品屋出租
科左后旗15㎡| 1室0廳 300元 面議 -

理想福園
科左后旗100㎡| 2室1廳 0元 面議 -
科左后旗200㎡| 6室1廳 0元 面議
-
 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
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 -
富源小區
科左后旗1000㎡| 20室2廳 0元 面議 -

博王御花苑
科左后旗90㎡| 2室1廳 0元 面議 -

金地鑫居
科左后旗69㎡| 2室1廳 1000元 面議 -

藍天下附近
科左后旗75㎡| 2室1廳 833元 面議 -

南區國稅小區
科左后旗90㎡| 3室1廳 11000元 面議

-
下一條:以守望者的虔誠傳承科爾沁文化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