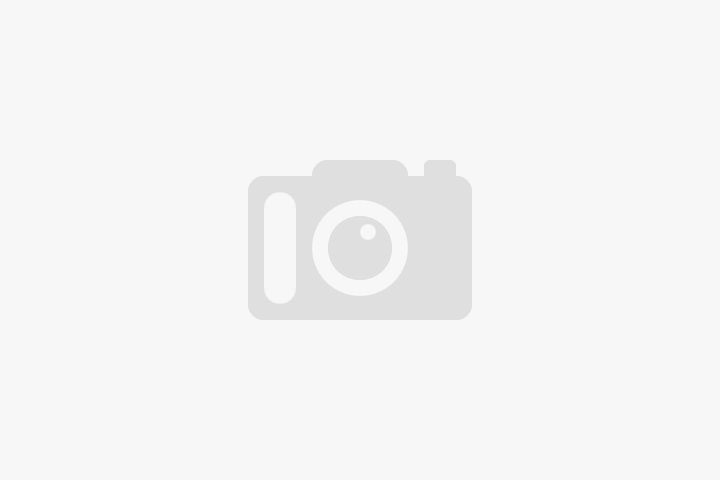微信掃一掃

老通遼回眸之三十_老通遼八景
舊時,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“八景”,也就是把八種最能代表城市特點的人文、自然景觀,分別起一個有詩意的名字。最著名的如老北京的“燕京八景”、杭州的“西湖八景”、南京的“金陵八景”,東北的錦州昔日也有“錦州八景”之說。各地所謂的八景,大都是文人騷客所為,是典型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。
通遼城歷史較短,缺少歷代遺存下來的古建筑和遺跡;最早來到這里的移民忙于商海拼搏,難免少了一點浪漫的文人情懷。但通遼這塊寶地水草豐美,四季分明,不乏長河落日,大漠孤煙之美。春有楊花柳絮,草色遙看近卻無;夏有古木蒼蒼,十里蛙聲動城郭;秋有沃野莊田,浩浩金風稻粱香;冬有九天飛絮,玉樹瓊枝野茫茫。塞外小城,宛如山野村妞,開朗,率真,不做作,不扭捏,充滿野性之美、自然之美,與那些名城故郡相比,別有一番韻味,有別人不具備的天然色彩,天人合一,古樸自然。因此,弄出一個屬于通遼人自己的“老通遼八景”,自有別樣意趣。
如今,隨著城市改造、擴張,昔日景物已難尋蹤跡。取而代之的,是寬闊的馬路,擁堵的汽車和一片片高樓大廈。撫今追昔,一些過來人難免唏噓感嘆。為此,筆者查閱文史資料,走訪古稀老人,同時,根據筆者當年所見所聞,擬定了“老通遼八景”,此八景分別是:
敖包走馬
落日飛鴉
春河流凌
柳林煙雨
金沙夕照
古樹長堤
月下蛙鳴
關廟榆錢
蒙古敖包位于和平路與西拉木倫大街西南角一帶,這座敖包在沒有建通遼鎮時就已經存在了。當時,曾有一道沙梁自西南向東北逶迤而去,這座蒙古敖包就坐落在沙梁南側。科爾沁蒙古族把這座敖包稱作“科爾沁的肚臍眼”,也就是科爾沁草原中心的意思。在巴林愛新荒丈放之前,每年夏天蒙古牧民都要在這里舉行一次那達慕,除了進行“男兒三藝”,即騎馬、射箭、摔跤比賽外,還要進行商品交易。通遼建城后,在敖包以北,即現在的西拉木倫公園、科爾沁賓館一帶建立了通遼縣苗圃。
1931年,日寇占領通遼,在敖包附近建了一座“蒙古忠魂塔”,用來祭奠被抗日軍民殺死的日本孤魂野鬼。同時,為了造成“滿蒙一體”“大東亞共榮圈”的假象,強行遷來幾戶蒙古人,在苗圃東南角,搭起蒙古包,每逢祭祀的日子,強行拉來城里的公職人員和“國高”學生湊數。同時,要蒙古人舉行騎馬、射箭、摔跤比賽。
1945年,日寇投降,忠魂塔被推倒,蒙古人遷走,這里一度歸于平靜。解放后,因為通遼城里沒有公園,苗圃東南角就成了人們周末休閑娛樂的地方。情侶在樹林深處喁喁交談,人們帶著孩子在枝影參差的樹下嬉戲,一派恬淡祥和景象。一直到1958年人民公園建成,這里也改建成果樹園。
出老北門——交通路與霍林河大街交匯口往北,路西有一片黑森森的樹林,樹木高大蒼黑,蓊蓊郁郁,樹梢上搭滿了老鴰窩。每到太陽西墜時分,西天邊落霞如錦,一片燦爛,宛如一張巨大的天幕,高大的樹木如剪影一般,歸巢的老鴰聚集在樹林上空,幾千只老鴰黑壓壓地在晚霞映襯下盤旋飛舞。這一幕,每天傍晚都要準時上演。
雖然黑樹林遠遠看上去郁郁蔥蔥,充滿生機,但人們卻很少到那里去。老北門是通往西遼河北岸的出口,出北門到城外辦事的人們走到這里,也不由得加快腳步,因為這里被人們稱之為“祭古寺”,也就是通遼城公共墓地。就在這樹木下面,一堆堆黃土,掩埋著死去的人們。路旁常會有新留下的紙錢,透過樹影間隙,總能看到那些新墳的墳頭上飄揚著白紙靈幡。在“祭古寺”南側,有幾間破敗的房子,青磚藍瓦,隱約可見當年的巍峨,這就是通遼建成不久的龍王廟。廟建成不久,香火不旺,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,成了看墳人的住地。所以,落日飛鴉景色雖美,卻只可遠觀,不能近玩。
老鴰,學名烏鴉,人們將其視為不詳之鳥,現在,有人脫口說出不吉利的話,仍會被人斥之為“烏鴉嘴”。究其原因,大概與老鴰食腐肉有關。那時候,戰爭、災害不斷,尸橫遍野、餓殍載道時有發生,老鴰就自覺擔負起“清道夫”的重任。人們對它的厭惡之心也由此產生。其實,究其歷史,老鴰也曾輝煌過,它是古代圖騰中的神鳥——太陽鳥。遠古巖畫上太陽圖案中間的那只鳥就是老鴰。老鴰的特點是“日出離巢,日暮回歸”,與太陽執行的是同一作息時間。京劇唱詞中的“金烏墜,玉兔升”,分別指的就是太陽月亮。
這一神鳥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卻險遭滅頂之災。當時,在大搞衛生的前提下,提出“消滅四害”,即“蒼蠅、蚊子、老鼠、麻雀”四種有害人類的動物。前三種主要是傳染疾病,麻雀則是糟害糧食。后來,有專家說,麻雀一年吃掉的害蟲所保護的糧食與他們吃掉的糧食相當,所以又把麻雀改為臭蟲,再改為蟑螂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。就在短短的時間里,消滅麻雀的槍口頻頻對準老鴰,致使老鴰在通遼一度絕跡。
當時,為了消滅麻雀,可謂煞費苦心,除了敲鑼打鼓把麻雀驚動起來以外,沒有鑼鼓的就把家里的臉盆、水桶等能敲響的東西拿出來,使勁敲擊,日夜不停,為的是讓麻雀不得安寧。同時,彈弓、氣槍齊上陣,搬梯子上房掏鳥窩,所有的手段一起施展出來對付小小的麻雀。麻雀畢竟體積小,飛得快,真正受害的卻是老鴰。老鴰成為獵殺對象還有一個原因,那就是外貿部門收購老鴰皮,受利益的驅使,很多人甚至打麻雀是假,而打老鴰是真正目的。
如今,生態環境不斷得到改善,很多多年不見的野生動物紛紛回歸。奇怪的是,過去通遼少見的喜鵲如今卻數量很多,甚至到城里筑巢,那些成群結隊,鋪天蓋地的老鴰已經難覓蹤影,成了難得一見的“稀有動物”。
西遼河,從南往北,再往東,把通遼城西、北兩側摟在懷里。站在西門外,西遼河大堤近在咫尺;出北門,行四五里就是遼河。當年的西遼河,水勢浩淼,聲聞數里。到了冬季,西遼河仿佛玩累了的巨龍,平靜而安詳。寒冷的西北風把大河凍成一米多厚的冰層,底下,潺潺流水在暗中涌動;厚厚的冰面上可以跑大車,走汽車。
春天來了,萬物萌動,生機一片。西遼河睡了一冬天,也被驚蟄的雷聲驚醒。先是在河岸邊,光溜溜的冰面開始解凍,化成晶瑩閃爍的水滴,不消幾天的工夫,冰面開始瓦解,大塊的冰漂浮在河面上,冰凌擁擠著、碰撞著,在河水的裹挾下,在河面上橫沖直撞,氣勢逼人。
大河開河時節,冰河又叫凌汛,尖利的冰塊對河岸威脅極大。除了事先加固堤岸,凌汛期間還要派人堅守,以防萬一。
此時,人們還沒有脫掉厚厚的冬裝,大棉襖、二棉褲,氈圪垯,皮烏拉,只有狗皮帽子早早地摘掉。人們站在大堤上,看冰河奔騰,猶如千軍萬馬疾馳而過,感受到的是屬于北方的豪爽大氣和雄渾壯闊。
隨著西遼河斷流,這一景觀已經成為歷史。雖然在大河里修了人工湖,但波瀾不驚的一汪碧水和昔日的西遼河相比,宛如一只小小的澡盆,只能令人望水興嘆。
老通遼,楊柳樹是當家樹,其次便是榆樹。最粗的兩株柳樹,在北門小學門前,幾個人環抱不過來,盛夏時節,樹蔭遮住身旁的教室和半條馬路;最大的一片柳樹林,西、南兩側連著西遼河大堤,南至霍林河大街,東至交通路西側。加上西遼河大堤旁高大的楊柳樹、祭古寺黑樹林,浩浩蕩蕩的一大片。
不同之處是,這片樹林不是高大的喬木,而是兩米多高的灌木叢。每到秋季,柳編匠人就到這里割柳條,把粗細適中的柳條割下來,回去編筐、籃、簍、笆。編精細的小筐,要選較細的柳枝,去掉皮。經巧手編制,會編出各種花樣,是婦女們的最愛。掛在自己屋子里的房笆,藏一些點心果品,同時,也是一件擺設。粗一些的柳條可以編土籃、柳條笆,結實耐用。
春天一到,柳樹林就迎來了生機,鋪天蓋地的綠色由淺變深,春風刮過,柳枝搖曳,滿目青翠。
小滿前后,是候鳥往北遷徙的季節,柳林是鳥的天堂,有的是由此路過,有的就在這里安家落戶,產卵孵雛。各種鳥兒或是在枝頭高聲鳴叫,或是躲在樹蔭里低吟淺唱,再加上相繼出現的“三叫驢”、蟈蟈和不知名的鳴蟲,寂靜的柳樹林變得十分熱鬧。
夏天,若遇上一場雨,柳樹林里就生出蘑菇,一叢叢、一片片,遍地都是。住在城邊的婦女們等不及雨停下來,就頭頂著柳條筐到樹林里撿蘑菇。
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,在柳樹林西北角建起靶場,八十年代末又在這里搞起了房地產開發,近些年,又修建起“奧體中心”,因此,那片鳥語蟲鳴的柳樹林就徹底從人們的視線里消失了。
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