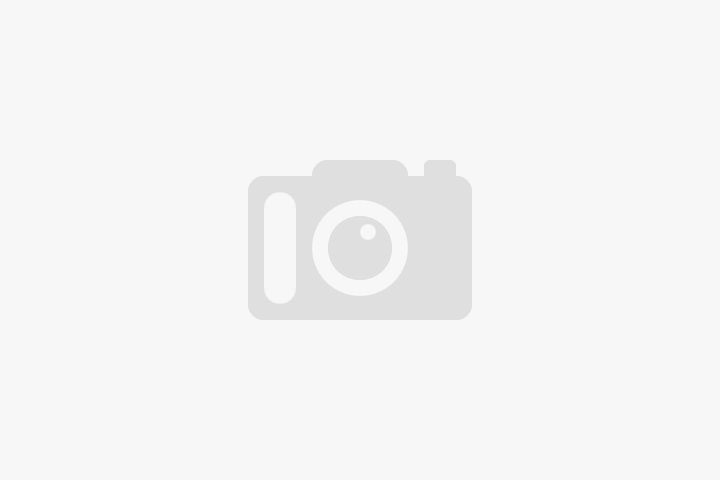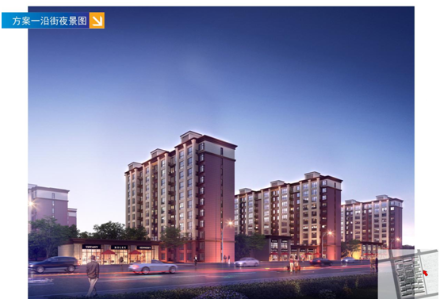微信掃一掃

老通遼回眸之二十四----南坨子“碉堡”留下的歷史疑問
記得我上小學時讀過一本不太厚的小說,叫《移花接木》,故事情節都忘記了,只記住有一個特務,裝扮成賣魚的,在臭魚爛蝦里放入了鼠疫菌。在這本書里還提到了內蒙古通遼。回想起來,那時的通遼就已成為“世界名城”了!那么,一個彈丸大的通遼是怎樣“成名”的呢?原因就是日本鬼子在通遼搞的鼠疫菌試驗!
去年秋季的一個午后,再次去森林公園。這一次本想去赴一場美麗的約會——早就聽說森林公園里有楓樹,又正逢中秋時節,不知楓葉是不是紅了。
進了公園,繞過一彎碧水,蜿蜒向西,一路上,秋水旖旎,波光瀲滟,沙丘起伏,秋葉婆娑。雖然秋季天氣已有些涼,但草木依舊蔥蘢,偶爾有幾片黃葉點綴其間,層林中就有了層次感,仿佛是一幅色彩厚重的油畫。
正邊走邊欣賞這旖旎的秋色,路旁,一幢灰色的建筑也隨著闖進眼簾,凝神細看,似曾相識。會是它嗎?那個留在我記憶中的“碉堡”!
小時候,就知道南沙坨有一座日本鬼子的“碉堡”,“碉堡”坐南朝北,南側有窗,北側有門。門是鐵的,掛著鎖。南沙坨雖然離城區很遠,但卻抵御不住它的誘惑,暑假里或秋天,同學們經常會結伴到這里來。有時候是來玩,也有的時候是來打草。借此,我們常常會爬到“碉堡”上去玩。
碉堡,是一種防御設施,通常應該建在交通要道和重要軍事防御區。曾經也看過真正的碉堡,他們就臥在鐵路旁,碉堡上向外射擊的洞孔像一只只失神的眼睛,不過,那些碉堡都是圓形的。可南坨子那座碉堡卻是方形的,只是頂部呈半圓形,上面也有圓孔,可圓孔有點小,看上去不像射擊用的,倒像是通氣孔。灰色的水泥墻體上還有明顯的模板的痕跡。
這個“碉堡”讓我感到怪異,因此,半個多世紀來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。我捉摸不透它到底是個什么東西,干什么用的。此刻,當遠遠地看見這個灰色怪物時,一時不敢斷定它是不是我記憶中的那座“碉堡”。
小路上,有一個年齡比我小的老太太領著小孫子,從外表看像是農村人。我以為她是南邊那個叫前坨子村的村民,就上前去問她,這是不是小鬼子建的那座碉堡,她說什么碉堡?不知道。我踏著沒膝深的荒草向怪物走去,老太太似乎也有了興趣,無奈小孫子執意向相反的方向跑。我到了“碉堡”前,聽到她在后面大聲問:“是嗎?”我說:“是!”她又問“有字嗎?”我說:“沒有。”
看起來,她更相信用文字寫成的歷史。
站在“碉堡”前,看它依舊是原來的模樣,好像歲月在這里停止了,只是在“碉堡”的頂部有用水泥抹過的新的痕跡。還有,它的南側和西側都被沙子埋住了。
我點著一支煙,坐在沙堆上揣摩著這個丑陋的東西,怎么看都覺得它不像是碉堡。我把目光投向南面,越過南坨子村再向南,應該有一座叫周家圍子的村莊,1943年,在那里曾經發生過一場慘烈的人間鼠疫,后來被專家學者認定為是日本侵略者搞的一次鼠疫試驗。
1943年7月,周家圍子有兩人突然死亡,人們還沒有反應過來這就是駭人聽聞的鼠疫,日本鬼子的防疫隊就進了村。他們先是封閉了圍子四周的大門,圍墻頂上每隔五米就有一個手持扎搶的保甲站崗放哨,村外還有警察在嚴格警戒,不準村民外出。
防疫隊每天兩次進村“摸疙瘩”,就是檢查腋下、大腿根有沒有淋巴腫大。不管男女老少,大姑娘小伙子、老公公兒媳婦,全部脫光,男女各站一排,面對面相對而立,挨個查體溫、摸疙瘩。摸出疙瘩的或體溫高的就被送進隔離所。有的人害怕,身子一哆嗦,就被說是得了鼠疫。
老鄉們回憶說,那時發生的事很蹊蹺。防疫隊總是在頭一天晚上就挖好坑,挖幾個坑,第二天準死幾個人。一個不多,一個不少。他們給村民打一種針,說是防疫針,但被打了針的,第二天準死!村民盧老八新婚不久,媳婦死后被日本人扒了皮。盧老八本來已經逃到村外,聽說后跑回村子和日本人算賬,拋飯碗打了防疫班的人,他們把盧老八捉住,打了一針,不到十分鐘,盧老八就死了。
孫玉富原本在鐵路工作,回來探家時,村子已經被封鎖,他只能一個人在村外玉米地里躲藏。他家共五口人,母親先被送進隔離所,死后被剝了皮。大弟弟聽說后整天哭,防疫隊說他得了鼠疫,也被送進隔離所,不久就死了。緊接著,父親和小弟弟也被關起來。
村子控制稍松一點后,孫玉富想回村看望父親,因在玉米地里被蚊蟲叮咬,身上已經沒好地方了,在圍子門前接受檢查時,也被送進隔離所。因此,他有機會看到隔離所里發生的一些怪事。他看到,一個廂房里有六七個鐵籠子,養的是“白耗子”。他在面的時候就看到過日本人給白耗子注射從人身上抽出來的血,也給人注射從白耗子身上抽出來的血;令他吃驚的是,廂房的墻根下放著大壇子,壇子里都是血水,上面漂著棉花。他好奇地挑起棉花,看到里面泡著的竟是人腦子、眼珠子……
村民回憶說,西門外放著四張大條桌,這四張桌子就是日本人的解剖臺。人死后,放在桌子上,日本人像殺豬一樣用水潑,有剝皮的、有開腦子的、有開膛破肚的。內臟挖出來后泡在藥水里,然后拿走。有的人還沒咽氣,就被活活解剖了。
就在這次“鼠疫”中,小小的周家圍子村一共死了179人。
從時間上判斷,防疫隊來得不算晚。從隔離手段上來看,也算嚴格。同時,又每天給村民打“防疫針”,為什么一個小小的村莊連鼠疫都沒有控制住,反而越演愈烈?
在周家圍子鬧鼠疫的同時,附近村莊也有鼠疫流行,那些村莊沒有被封鎖隔離,反倒沒有死那么多的人。
種種跡象表明,這是小鬼子在周家圍子搞的一次鼠疫試驗,是活生生的人體試驗!
我的思路從周家圍子收回來,眼看著這座怪異的“碉堡”。
這里地處南沙坨子中心,四周都是漫漫黃沙,沒有交通要道需要據守,顯然,它不是軍事防御設施。
以前曾聽老年人講,當年,這里戒備森嚴,周圍有電網,有巡邏哨,老百姓根本無法靠前。
會是彈藥庫嗎?根本不可能!這里連汽車都難以通行。況且,日軍當年的火藥庫就設在城里,位于老爺廟西二百米處。日本鬼子逃走時,已經來不及將它們帶走。1945年,地方維持會防御土匪進攻時,所使用的彈藥就有一部分來自這座火藥庫。
唯一的可能,這里是小鬼子存放鼠疫菌的倉庫!
內蒙古東部屬于鼠疫發源地,以前也有鼠疫發生,但都有一定的周期性。自從日本鬼子進了東北,這里的鼠疫就接連不斷。罪惡的七·三一部隊所犯下的罪行已是世人皆知。1945年8月,日本鬼子宣布投降,他們臨逃跑時,又把鼠疫、傷寒等細菌以及劇毒品投放到存放的大米白面里面,另外,還派特務把含毒菌的玩具、糖果等送給小孩,還往水井里投放疫菌。
小鬼子喪心病狂的舉動,使我軍民遭受了巨大傷亡,他們反人類的罪行也受到全世界正義聲音的譴責。
時間已經過去60多年,昔日劊子手們制造罪惡的刑場已恢復平靜,但日本鬼子留給中國人民的傷痛卻始終無法愈合。
不論這里是不是他們存放疫菌的地方,但肯定是他們制造罪惡的地方。在綠草如茵的森林公園,這個“碉堡”就像長在一塊碧玉上的膿瘡,讓人厭惡。但還必須留著它,因為它是歷史的見證。他告訴我們,時間可以流逝,但歷史不能遺忘。如果事實真的如此,我建議,這里應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課堂,告訴后人永遠不要忘記這血的恥辱,一個健忘的民族和一個落后的民族一樣,沒有出息!
-

富源豪庭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華府在售
科左后旗 33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寶典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恒益·悅城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清華里在售
科左后旗 33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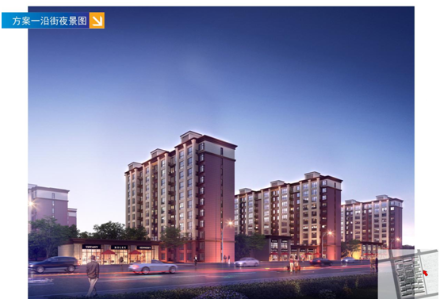
逸品藍山Ⅱ期在售
科左后旗 31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怡景嘉園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福園(理想家園B區)在售
科左后旗 30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郡府在售
科左后旗 3935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富源龍庭待售
科左后旗 409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博王·昊龍公館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甘旗卡商業廣場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
-

博王新村
科左后旗200㎡| 6室6廳 0元 面議 -

團結東區
科左后旗130㎡| 6室2廳 0元 面議 -
溫州商城二樓精品屋出租
科左后旗15㎡| 1室0廳 300元 面議 -

理想福園
科左后旗100㎡| 2室1廳 0元 面議 -
科左后旗200㎡| 6室1廳 0元 面議
-
 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
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 -
富源小區
科左后旗1000㎡| 20室2廳 0元 面議 -

華麗西區
科左后旗58㎡| 1室1廳 900元 面議 -

綠園小區(巴彥路)
科左后旗86㎡| 2室1廳 792元 面議 -

藍天下法院家屬樓
科左后旗80㎡| 2室1廳 1000元 面議
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