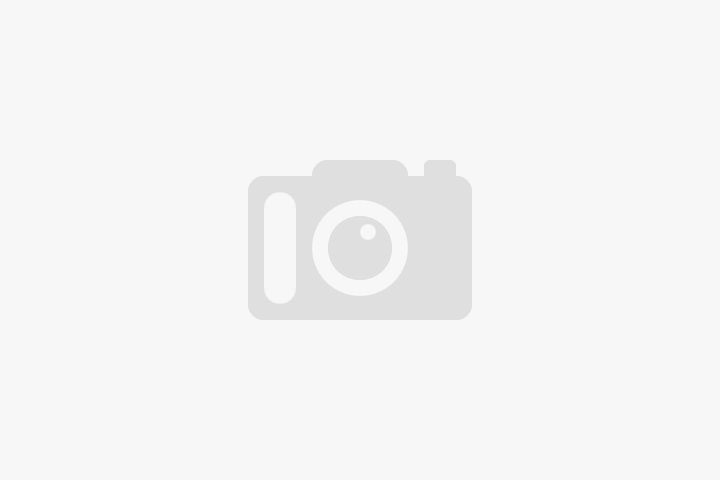正在閱讀:老通遼回眸之十九-通遼早年的茶俗與茶館
分享文章
微信掃一掃
參與評論
0

信息未審核或下架中,當前頁面為預覽效果,僅管理員可見
老通遼回眸之十九-通遼早年的茶俗與茶館
轉載
![]() mingyu于 2016/05/26 21:53:48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2800 閱讀
0 評論
2 點贊
mingyu于 2016/05/26 21:53:48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2800 閱讀
0 評論
2 點贊
茶館,是以喝茶為內容的場所。在茶文化歷史悠久的中國,自古至今,從煙雨江南到塞外北疆,飲茶之風久盛不衰。飲茶講究的是個過程,注重一個“品”字。但是,正所謂十里不同風,百里不同俗,因地域、氣候、飲食習慣的迥異,各地飲茶方式和賦予飲茶的文化內涵也大不相同。
通遼地處內蒙古東部,一百多年前,這里是蒙古人的牧場。隨著清末“移民實邊”政策的實施以及后來軍閥掠奪草地,大批漢人及其他民族也涌入草原,這里開始了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和融合,加之受周邊遼寧、吉林風氣影響,便創造出了只屬于這片土地獨有的茶文化現象。
在內蒙古,無論是蒙族人還是漢族人管飲茶都不叫飲茶,而叫喝茶,這不僅僅是表述不同,也是喝茶方式和喝茶目的不同,就是說喝茶更注重其實際。
蒙古人喜歡喝奶茶,奶茶要用茶磚。茶磚是經過一道工藝把茶葉壓制成為方磚形狀,再晾干,目的是便于攜帶和保存。與沏茶、泡茶不同的是,奶茶講究“熬”,據說熬奶茶要經過七道程序。過去,蒙古婦女要在太陽出來之前就用牛糞火把茶熬開,再用瓢將茶反復揚九九八十一下,之后再放入事先炒好的小米。澄清后,把茶渣、小米濾出去,再加黃油和牛奶熬上兩個開,奶茶才算熬制成功。據說,因手法不同,每個人熬出來的奶茶味道都不一樣。
蒙古人更擅飲茶,尤其對紅茶情有獨鐘。這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有關。蒙古人多以游牧為生,飲食以肉食為主,但難以消化,而紅茶卻有助消化的功能。在歷史上,明朝政府曾把茶葉當做控制蒙古人的重要武器,茶葉的銷售、運輸都有中央政府統一控制,動輒以斷茶相威脅,既有因茶葉保持邊疆穩定,也曾因茶葉引發戰爭。
喝茶的人都知道喝紅茶會上癮,但與吸食毒品上癮不是一回事。人犯了“茶癮”,會感到渾身不適。早年,蒙古人出遠門身上總會帶上幾樣東西:一個繡著五彩飄帶的裝旱煙的口袋,一支長桿旱煙袋,一個裝沙槍火藥和槍沙的口袋;再有,就是茶葉口袋。茶癮大的人在途中走的饑渴難耐又沒水沏茶時,就會捏一撮紅茶放在嘴里嚼一嚼,以此來解渴又解茶癮。
后來的漢人受蒙古人影響,也開始喝紅茶。有錢人喝高檔的,窮人喝茶粉、茶末。家里來了親戚,先遞煙笸籮、旱煙袋,然后趕緊燒水沏茶,這是絕不能少的規矩,否則就被認為不熱情。可是,過去不比現在,那時要用明火燒水。夏天熱,看到大家都懶得燒水,有頭腦好使的就在胡同里支起個茶爐,這也是初始的茶館。不過,這種茶館只賣“走水”,不設茶座。等到了冬季,家家燒火取暖,不再出去打水,胡同的茶館自然暫時歇業,等明年春暖花開時再重新開張。
當然,也有真正的茶館,但都在主要商業大街或居民密集的商業區。如明仁大街、北市場、南市場這些熱鬧的地方。茶館的標志是在門前電線桿上或樹上,挑著一只破洋鐵壺,壺底上拴著一根紅布條,權當幌子。茶館門面一般都不大,通常只有一間房,一進門的墻角立著一個大水壺,有一根一寸粗的管子從水壺頂上通往窗外。鐵管子里有簧片,水開了,蒸汽吹動簧片發出“吱兒吱兒”的響聲,代替了吆喝。
屋里白灰刷墻,屋頂多糊著“窩紙”——一種印著單色圖案的糊棚紙。沿著兩側的墻壁擺著兩溜桌子、長條板凳。本色無漆,因為常和水打交道,倒也干凈。
茶館大都是夫妻店,沒有店小二、茶博士之類。來了客人,掌柜上前打招呼,同時,按人頭把茶碗放在客人面前。茶碗不大,粗磁,杯口有兩道藍邊。掌柜問:“帶葉子沒有?”
“葉子”,就是茶葉。如果自帶茶葉,掌柜接過去沖好水送過來。如果沒帶,掌柜問“要好的,還是茶末?”
沏茶用的是磁茶壺,喝一碗倒一碗。水喝得差不多,喊一聲“續水!”掌柜就過來把水續滿。
到茶館喝水叫“下茶館”,跟下飯館相提并論。下茶館的有各色人等,進城辦事或購物的農牧民,少不得要下茶館。顛簸了一路,走渴了,就會走進茶館沏上一壺茶,有的帶著干糧進城的,到茶館要一壺茶,邊吃邊喝。城里人也有一部分喜歡下茶館,圖的是那里的氛圍。大家本不相識,幾句話嘮得投機就成了朋友,天南海北,云山霧罩。也有約朋友下館子出來再進茶館的,以前的飯館是只能吃飯不管水,不像現在的飯館,一落座服務員就沏上茶送過來,直到吃完飯,茶水保證供應。所以,幾個朋友下完館子,想喝水就得上茶館。
在很多地方的茶館里都有小吃,朱自清在《說揚州》里就寫過揚州茶館里的小吃:“小籠點心,肉餡兒的,蟹肉餡兒的,筍肉餡兒的且不用說,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燒麥,還有干菜包子。菜選那最嫩的,剁成泥,加一點兒糖一點油,蒸得白生生的,熱騰騰的,到口輕松地化去,留下一絲兒余味。”文中還寫道:老包頭的茶館里專門賣燒麥,有的也寫成燒美、燒梅,生意人早起到茶館一邊就著茶水吃燒賣,一邊交換著商業信息,可謂一舉兩得。不過,通遼的茶館沒有小吃,想吃東西,要么自帶,要么由掌柜去代買。通遼茶館里最常見的食品,是一種叫爐果的糕點。爐果是白面做的,長不到兩寸,端面五六分見方,經烤制,酥脆且別具風味。喝茶水,吃爐果,是老通遼一景,不論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,大都喜歡這一口。
茶館聚集的人多,自然是各種消息的發布中心。閑來沒事,聊一聊小道消息,奇聞軼事,從物價漲落,到土匪擾民;從縣衙貪賄,到小偷落網,無所不談。有了這樣的便利條件,茶館就有了一種不為外人所知的功能——給警察局當密探。有了什么消息線索,都要報告給警察。
不過,在日偽統治時期,茶館里天南地北地侃大山便戛然而止。那個時期不用說人們食不果腹,肚子里沒油水,就是那些有頭有臉吃喝不愁的,下茶館也得小心翼翼,生怕哪句話說走了嘴,就立即被當成危險份子、政治犯抓走。所以沒有幾個人再有閑情逸致下茶館,誰愿意因為兩句閑嗑去喝辣椒水,坐老虎凳,甚至掉腦袋呢!掌柜的也會受連累。就是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沒消停,墻上、柱子上總會有白紙黑字提醒你“莫談國事”。偶爾有人說話沾惹到敏感話題,茶館掌柜馬上會過來附耳告訴你:“兩位爺別說了,我這一家子還指著這個吃飯呢!”
由于日偽統治時期商業被高度壟斷,大部分商品實行“專賣制”,經濟蕭條,生意難做,茶館也相繼關門,因此,臨街房屋十室九空。
1947年,通遼解放后,政府大力號召商戶開門營業,因開茶館本錢小,所以,恢復得也快。在現在的明仁大街路南很快就有幾家茶館相繼開門營業。建國后,隨著臨街商鋪興起,茶館業更加興旺了起來。
產業有產業鏈,商業也有商業鏈。茶館,也催生了另外一個職業——送水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,通遼市內就有專門以送水為生的人,他們一根扁擔,兩只水桶,走街串戶為居民送水。同時,負責水井維護修理。那時的水井叫洋井,一根井管直接插入地下出水區,最深處的管都被打上小窟窿,好讓水進入水管,但需要纏上棕樹皮用以隔離沙土。但時間久了水管還是會腐爛,導致水井“反沙”等, 壓出來的水就是混的,不能食用,挑水的就會挨家挨戶收錢幫著維修。給居民送水是有時間也是有數量的,一般半天就能送完。下午,就可以拎上鐮刀,扛著扁擔到郊外去割草,再賣給城里養牲口的人家。但有了茶館,因茶館營業時間長,給茶館送水就沒有了富裕時間,當然收入也增加了。
那時候,茶館要準備“水牌子”,就是用包裝盒剪成的方形硬紙片,蓋上圖章,一挑水付給一個水牌子,用以兌付現錢。好在那時人心醇厚,不會造假,否則,這么簡單的“流通券”是很容易仿制的。
社會進步也反映在送水的身上,到上世紀六十年代,送水的放下扁擔,改用手推車。用一只汽油桶橫著放在車上,汽油桶上有注水口、一截自行車內胎做放水口,一次可以裝100公斤水,不但一次能多送不少水,還節省了不少體力。
通遼城里送水最“有名”的要數一個叫“胡傻子”的人,他不是十分呆傻,只是心眼兒來得慢。此人個頭不算高,很結實,因為家中有老娘,穿著還算整齊。他在城里最繁華的明仁大街中段一百貨一帶送水,所以大家都認識他。他就是靠送水養活自己和老娘,給老娘養老送終的。
為了招攬顧客,茶館里一般都準備象棋,有的茶館還會預備好幾副。有時,幾張桌子前圍滿人,默默觀棋的,七嘴八舌支招的,更有喧賓奪主動手的,十分熱鬧,給茶館增添不少人氣。應該說,老通遼的茶館起到了象棋沙龍的作用,不少人在茶館里學象棋、下象棋,茶館不僅是賣茶喝水的地方,還帶動了通遼市象棋的發展,發展了許多象棋愛好者,甚至不乏棋壇高手。
通遼地處內蒙古東部,一百多年前,這里是蒙古人的牧場。隨著清末“移民實邊”政策的實施以及后來軍閥掠奪草地,大批漢人及其他民族也涌入草原,這里開始了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和融合,加之受周邊遼寧、吉林風氣影響,便創造出了只屬于這片土地獨有的茶文化現象。
在內蒙古,無論是蒙族人還是漢族人管飲茶都不叫飲茶,而叫喝茶,這不僅僅是表述不同,也是喝茶方式和喝茶目的不同,就是說喝茶更注重其實際。
蒙古人喜歡喝奶茶,奶茶要用茶磚。茶磚是經過一道工藝把茶葉壓制成為方磚形狀,再晾干,目的是便于攜帶和保存。與沏茶、泡茶不同的是,奶茶講究“熬”,據說熬奶茶要經過七道程序。過去,蒙古婦女要在太陽出來之前就用牛糞火把茶熬開,再用瓢將茶反復揚九九八十一下,之后再放入事先炒好的小米。澄清后,把茶渣、小米濾出去,再加黃油和牛奶熬上兩個開,奶茶才算熬制成功。據說,因手法不同,每個人熬出來的奶茶味道都不一樣。
蒙古人更擅飲茶,尤其對紅茶情有獨鐘。這與他們的生活方式有關。蒙古人多以游牧為生,飲食以肉食為主,但難以消化,而紅茶卻有助消化的功能。在歷史上,明朝政府曾把茶葉當做控制蒙古人的重要武器,茶葉的銷售、運輸都有中央政府統一控制,動輒以斷茶相威脅,既有因茶葉保持邊疆穩定,也曾因茶葉引發戰爭。
喝茶的人都知道喝紅茶會上癮,但與吸食毒品上癮不是一回事。人犯了“茶癮”,會感到渾身不適。早年,蒙古人出遠門身上總會帶上幾樣東西:一個繡著五彩飄帶的裝旱煙的口袋,一支長桿旱煙袋,一個裝沙槍火藥和槍沙的口袋;再有,就是茶葉口袋。茶癮大的人在途中走的饑渴難耐又沒水沏茶時,就會捏一撮紅茶放在嘴里嚼一嚼,以此來解渴又解茶癮。
后來的漢人受蒙古人影響,也開始喝紅茶。有錢人喝高檔的,窮人喝茶粉、茶末。家里來了親戚,先遞煙笸籮、旱煙袋,然后趕緊燒水沏茶,這是絕不能少的規矩,否則就被認為不熱情。可是,過去不比現在,那時要用明火燒水。夏天熱,看到大家都懶得燒水,有頭腦好使的就在胡同里支起個茶爐,這也是初始的茶館。不過,這種茶館只賣“走水”,不設茶座。等到了冬季,家家燒火取暖,不再出去打水,胡同的茶館自然暫時歇業,等明年春暖花開時再重新開張。
當然,也有真正的茶館,但都在主要商業大街或居民密集的商業區。如明仁大街、北市場、南市場這些熱鬧的地方。茶館的標志是在門前電線桿上或樹上,挑著一只破洋鐵壺,壺底上拴著一根紅布條,權當幌子。茶館門面一般都不大,通常只有一間房,一進門的墻角立著一個大水壺,有一根一寸粗的管子從水壺頂上通往窗外。鐵管子里有簧片,水開了,蒸汽吹動簧片發出“吱兒吱兒”的響聲,代替了吆喝。
屋里白灰刷墻,屋頂多糊著“窩紙”——一種印著單色圖案的糊棚紙。沿著兩側的墻壁擺著兩溜桌子、長條板凳。本色無漆,因為常和水打交道,倒也干凈。
茶館大都是夫妻店,沒有店小二、茶博士之類。來了客人,掌柜上前打招呼,同時,按人頭把茶碗放在客人面前。茶碗不大,粗磁,杯口有兩道藍邊。掌柜問:“帶葉子沒有?”
“葉子”,就是茶葉。如果自帶茶葉,掌柜接過去沖好水送過來。如果沒帶,掌柜問“要好的,還是茶末?”
沏茶用的是磁茶壺,喝一碗倒一碗。水喝得差不多,喊一聲“續水!”掌柜就過來把水續滿。
到茶館喝水叫“下茶館”,跟下飯館相提并論。下茶館的有各色人等,進城辦事或購物的農牧民,少不得要下茶館。顛簸了一路,走渴了,就會走進茶館沏上一壺茶,有的帶著干糧進城的,到茶館要一壺茶,邊吃邊喝。城里人也有一部分喜歡下茶館,圖的是那里的氛圍。大家本不相識,幾句話嘮得投機就成了朋友,天南海北,云山霧罩。也有約朋友下館子出來再進茶館的,以前的飯館是只能吃飯不管水,不像現在的飯館,一落座服務員就沏上茶送過來,直到吃完飯,茶水保證供應。所以,幾個朋友下完館子,想喝水就得上茶館。
在很多地方的茶館里都有小吃,朱自清在《說揚州》里就寫過揚州茶館里的小吃:“小籠點心,肉餡兒的,蟹肉餡兒的,筍肉餡兒的且不用說,最可口的是菜包子菜燒麥,還有干菜包子。菜選那最嫩的,剁成泥,加一點兒糖一點油,蒸得白生生的,熱騰騰的,到口輕松地化去,留下一絲兒余味。”文中還寫道:老包頭的茶館里專門賣燒麥,有的也寫成燒美、燒梅,生意人早起到茶館一邊就著茶水吃燒賣,一邊交換著商業信息,可謂一舉兩得。不過,通遼的茶館沒有小吃,想吃東西,要么自帶,要么由掌柜去代買。通遼茶館里最常見的食品,是一種叫爐果的糕點。爐果是白面做的,長不到兩寸,端面五六分見方,經烤制,酥脆且別具風味。喝茶水,吃爐果,是老通遼一景,不論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,大都喜歡這一口。
茶館聚集的人多,自然是各種消息的發布中心。閑來沒事,聊一聊小道消息,奇聞軼事,從物價漲落,到土匪擾民;從縣衙貪賄,到小偷落網,無所不談。有了這樣的便利條件,茶館就有了一種不為外人所知的功能——給警察局當密探。有了什么消息線索,都要報告給警察。
不過,在日偽統治時期,茶館里天南地北地侃大山便戛然而止。那個時期不用說人們食不果腹,肚子里沒油水,就是那些有頭有臉吃喝不愁的,下茶館也得小心翼翼,生怕哪句話說走了嘴,就立即被當成危險份子、政治犯抓走。所以沒有幾個人再有閑情逸致下茶館,誰愿意因為兩句閑嗑去喝辣椒水,坐老虎凳,甚至掉腦袋呢!掌柜的也會受連累。就是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沒消停,墻上、柱子上總會有白紙黑字提醒你“莫談國事”。偶爾有人說話沾惹到敏感話題,茶館掌柜馬上會過來附耳告訴你:“兩位爺別說了,我這一家子還指著這個吃飯呢!”
由于日偽統治時期商業被高度壟斷,大部分商品實行“專賣制”,經濟蕭條,生意難做,茶館也相繼關門,因此,臨街房屋十室九空。
1947年,通遼解放后,政府大力號召商戶開門營業,因開茶館本錢小,所以,恢復得也快。在現在的明仁大街路南很快就有幾家茶館相繼開門營業。建國后,隨著臨街商鋪興起,茶館業更加興旺了起來。
產業有產業鏈,商業也有商業鏈。茶館,也催生了另外一個職業——送水。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,通遼市內就有專門以送水為生的人,他們一根扁擔,兩只水桶,走街串戶為居民送水。同時,負責水井維護修理。那時的水井叫洋井,一根井管直接插入地下出水區,最深處的管都被打上小窟窿,好讓水進入水管,但需要纏上棕樹皮用以隔離沙土。但時間久了水管還是會腐爛,導致水井“反沙”等, 壓出來的水就是混的,不能食用,挑水的就會挨家挨戶收錢幫著維修。給居民送水是有時間也是有數量的,一般半天就能送完。下午,就可以拎上鐮刀,扛著扁擔到郊外去割草,再賣給城里養牲口的人家。但有了茶館,因茶館營業時間長,給茶館送水就沒有了富裕時間,當然收入也增加了。
那時候,茶館要準備“水牌子”,就是用包裝盒剪成的方形硬紙片,蓋上圖章,一挑水付給一個水牌子,用以兌付現錢。好在那時人心醇厚,不會造假,否則,這么簡單的“流通券”是很容易仿制的。
社會進步也反映在送水的身上,到上世紀六十年代,送水的放下扁擔,改用手推車。用一只汽油桶橫著放在車上,汽油桶上有注水口、一截自行車內胎做放水口,一次可以裝100公斤水,不但一次能多送不少水,還節省了不少體力。
通遼城里送水最“有名”的要數一個叫“胡傻子”的人,他不是十分呆傻,只是心眼兒來得慢。此人個頭不算高,很結實,因為家中有老娘,穿著還算整齊。他在城里最繁華的明仁大街中段一百貨一帶送水,所以大家都認識他。他就是靠送水養活自己和老娘,給老娘養老送終的。
為了招攬顧客,茶館里一般都準備象棋,有的茶館還會預備好幾副。有時,幾張桌子前圍滿人,默默觀棋的,七嘴八舌支招的,更有喧賓奪主動手的,十分熱鬧,給茶館增添不少人氣。應該說,老通遼的茶館起到了象棋沙龍的作用,不少人在茶館里學象棋、下象棋,茶館不僅是賣茶喝水的地方,還帶動了通遼市象棋的發展,發展了許多象棋愛好者,甚至不乏棋壇高手。
贊
已有0人點贊
找對象
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