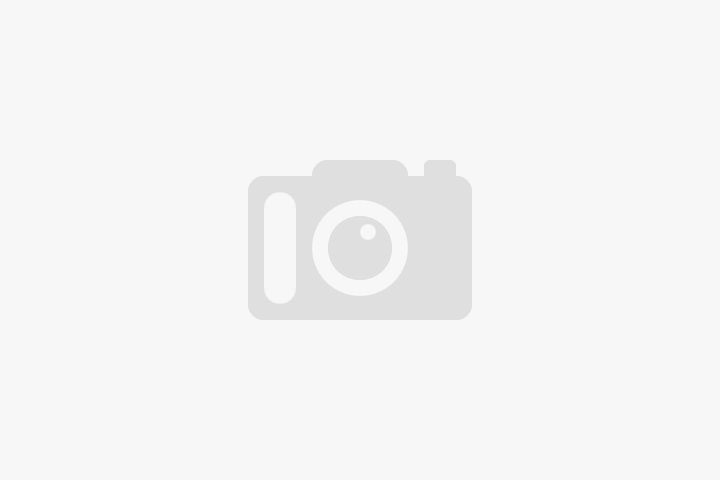正在閱讀:回眸老通遼之十七-閑話通遼老澡堂子
分享文章
微信掃一掃
參與評論
0

信息未審核或下架中,當前頁面為預覽效果,僅管理員可見
回眸老通遼之十七-閑話通遼老澡堂子
轉載
![]() mingyu于 2016/05/20 15:52:31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5774 閱讀
0 評論
1 點贊
mingyu于 2016/05/20 15:52:31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5774 閱讀
0 評論
1 點贊
澡堂子,就是浴池。如今走在大街上,隨處可見。尤其是現在的賓館、會館、足療城,連小招待所也設有對外營業的浴池。居家也都有了專門的衛生間,什么太陽能、過水熱、電淋浴器等洗浴設施家家具備,想怎么洗怎么洗,想什么時候洗就什么時候洗,所以說,洗澡,對當代人來說已不算什么事兒,更談不上是大事兒。但退回到幾十年前卻不是這樣。
三十多年前,因為經濟條件差,住房困難,根本談不上衛生設施。加上家里人口多,那時十幾口之家多的是,人口少的也得五六口。好多人家都是三代同堂,幾乎所有人家都是兩代人同居一室,住南北大炕,甚至兩戶人家擠在一間屋子里也不罕見,這樣的境況,洗把臉都費勁,就別說洗澡了。說起來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相信,從解放前到改革開放前,通遼城里只有一家澡堂子,而且是私人產業,解放后歸為了國有,改為了國營。
說起澡堂子,那得要從通遼建鎮說起。通遼建鎮之初就有了南市場、北市場兩處飯館和妓院、劇場等場所。為適應需求,澡堂子也應運而生,這第一所澡堂子就建在了南市場。后來,有一個叫劉居正的在北市場附近又建了一座浴池,至此,通遼城里有了一南一北兩個澡堂子。
劉居正,有資料說是當年私建小街基的劉振廷的兒子。其身份為“退役日偽少將”。其實,建北澡堂子時,日寇還沒有侵占東北。但他在日偽時期成為漢奸卻是事實。通遼歷史資料里,對劉居正是有所記載的:1945年8月15日,通遼成立“地方治安維持會”,日偽少將劉居正任會長;10月15日,成立通遼縣臨時政府,劉居正為代理縣長。1946年3月20日至24日,中共通遼中心縣委提議召開了臨時參議會,其中,議程里有“清算漢奸劉居正、沈子奇等人罪行”。
劉居正不僅修建澡堂子,還在北市場開妓院,并建過一座磚木結構的戲樓,后在一場大火中被燒毀。此人解放后被鎮壓。這些雖為題外話,但隨著劉居正的被鎮壓,他建的澡堂子也隨之停業散攤。通遼城從此就僅剩下一個澡堂子了。
在當時,澡堂子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夠經常光顧的地方。一般人不趕上特殊情況都不會去澡堂子洗澡,因為去洗一次澡要花三毛錢呢。三毛錢說起來不多,但那是當時一般工人一天工資的四分之一啊,是一家人一天足夠吃菜的錢。所以,要想洗澡,就去西遼河天然大浴池。夏季,每天都有很多人泡在西遼河里,人們撲騰一陣,連消暑帶洗澡,一舉兩得。講究點兒的回來的路上,找一口水井,用柳罐斗提上沁涼的井水從頭到腳澆上一遍,會更舒適。但美中不足的是這個天然浴池有時令性,只有夏天才行,春秋水太涼,冬季就成了冰場。女人要想洗澡就更加困難,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躲在角落處偷偷擦一擦。
那些賣苦力的每天都弄得一身汗、一身泥,但大多數人也只有到過年時,才會去一次澡堂子。
澡堂子里有專人招呼顧客,他們是澡堂子里為數不多算穿衣服的人。他們有一個習慣,喜歡在頭上扎一條白毛巾,毛巾扎法既不同于山東人,也不同于“偷地雷”的河北人,他們是把毛巾縷起來,從腦后攏過來,在腦門上系一個扣,在當時這也成了他們的行業標志。
進了澡堂子,墻上寫著“貴重物品交柜保管”字樣。手表、金錢等不交柜,損失自負;大廳里有幾排兩兩相對的床,床頭有一只小柜。
澡堂子最初沒有淋浴,只有一大一小兩個貼著瓷磚的池子,大池子里水溫稍低。那時洗澡,講究“泡”。坐在熱水池子里,一泡就是老半天,直到渾身燙得發紅才算過癮。澡堂子的好處之一就是,凡是進了屋,都脫得一絲不掛,沒有了貴賤之分,地位之別。百姓官員、警察小偷、掌柜伙計、車夫兵痞,一律“赤誠相見”,毫不掩飾。去洗澡的人澡堂子會給每人發一條浴巾,有的人松松垮垮地圍在腰上,擋住“要害”,也有人不用,泡夠了,到大廳里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覺。也有人要上一壺“葉子”,半斤果子,連吃帶喝,還有就在澡堂子里下棋的,休閑自在夠了,然后回去再泡。
雖然說大家都光著身子,身份平等,但是從膚色上還是大致能看出差異:有渾身上下皮膚細白的,有兩頭黑中間白的。從皮膚上就能大概猜得出他們的職業,白嫩的,不是商店掌柜伙計,也是機關文員;而那些一身腱子肉,除了被短褲常年遮掩的部位以外通體黝黑的,自然是干力氣活的。
有了澡堂子,就有了常客。一些有閑錢又有閑工夫的人往往吃飽了早飯,就早早去澡堂子,因為這時的水干凈。澡堂子里的水往往從早到晚一天不換,如果去得晚了,水就像泥漿一樣,有人調侃說,水稠得像 子一樣,連腳都伸不進去。
澡堂子還是唱歌的好地方。有人專門喜歡在澡堂子里唱歌、唱戲,時人稱“澡堂子唱手”。澡堂子里不論地面、墻壁、水池子,除了水泥就是瓷磚,所以攏音,猛地一嗓子,經反射后的聲音分外好聽。另外,或許是澡堂子里的蒸汽對嗓子也有幫助,好多人一到澡堂子,嗓子就“開了”,感覺唱出的聲音比在外面唱得好聽多了。因此,有些人想唱歌也會去澡堂子洗澡。
要說那時的澡堂子設施雖然沒有現在的高檔浴池好,但服務設施和質量卻不比如今差。不但有專門搓澡的師傅,他們還統一著裝,半袖淺藍色上衣,配白色短褲。那時當搓澡師需要專門拜師學藝。好的搓澡師傅講究的是手法,一條毛巾纏在手上,從臉開始,額頭、臉頰、耳根、脖子,依次往下,一直到腳。不同的皮膚用不同的力度,毛巾搓在身上,剛柔相濟,擦得皮膚微紅,渾身舒坦。搓澡師傅還擅長按摩推拿,在各關節和穴道上敲擊一遍,能擊打出花點,節奏鮮明,富有樂感。最后是抻指頭,把顧客的十個手指依次抻一遍,每抻一下,“啪”地一聲脆響。一套搓、敲、抻、按下來,保你遍體的骨頭松散,睡意朦朧。
澡堂子里還專設一間小屋,是給剃頭師傅預備的。很多人在澡堂子里洗完澡順便就剃頭,在這兒剃頭有一樣好處,就是省去洗頭這一層。
俗話說,“飽了不剃頭,餓了不洗澡”。剃頭難免要低頭彎腰,剛剛吃飽了去剃頭,肚子窩著不舒服;而洗澡消耗體力,餓了洗澡,容易頭暈眼花。可澡堂子里卻真的把這兩個行當合在了一起。可有一樣,凡是要剃頭的,都是先洗澡,等肚子里的東西消化得差不多了才去剃頭。
澡堂子里除了洗澡、剃頭還有修腳師傅。洗澡后腳干凈,沒有臭味,同時,腳底也泡軟了,好干活。那時的鞋襪遠不如現在的舒服合腳,加上“扛大個”的、推膠車的、出力氣的人走路多,又負重,很容易得腳疾,最多的是長雞眼、腳趾甲畸形。江湖上也有專治雞眼的,地上鋪一塊白布,用墨水畫著腳上的各種疾病,為的是做廣告,有來修腳的,就在當街把腳搬起來,放在自己的大腿上,用小尖刀往外摳雞眼、修腳趾甲,鮮血淋漓,看著 人。因此,更多的人愿意到澡堂子修腳,是因為既衛生又安全。
修腳師傅與理發匠、澡堂師傅、櫥子、跑堂等都屬于服務行業。按舊社會的說法叫“伺候人的”,都屬于“下九流”之列。惟獨修腳師傅卻是上九流。有一種說法,說是其他屬于下九流的“伺候人”時都要站著,修腳師傅則不然,即便是給王侯將相,甚至皇上修腳,也得坐著。你想,能和皇上“平起平坐”,地位能低得了嗎?
按舊俗,各行各業都要有祖師,澡堂子也不例外。各地澡堂子供奉的祖師不盡相同,有的供葛洪,就是自號抱樸子的煉丹家、醫藥學家。老通遼澡堂子供奉的祖師爺是姜子牙。老東北門有一戶澡堂世家,每逢春節,都要在西房山豎起一根旗桿,旗桿上有刁斗,下有神龕,點著香燭。姜子牙是封神榜上的人物,封神時把所有的神都封完了,卻忘了自己,只得將自己封在旗桿之下。至于他如何成為澡堂業的祖師不得而知。
解放后,澡堂子改成了通遼“國營浴池”,地點就在“圈樓”步行街西南角,上世紀八十年代市政府改造露天市場,建起“圈樓”及幾幢樓房,惟獨浴池沒有動。一座破舊二層小樓在那里堅持了多年。
隨著城里人口不斷增多,國營企業職工每人每月發一張澡票。同時,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,加上政府號召大搞“愛國衛生運動”,洗澡的人成倍增加,浴池里每天人滿為患,但浴池卻沒有因此增加,依舊是一花獨秀,一直到近三十年才遍地開花。
不過,上個世紀六十年代,市里較大的企業,如農機廠等已建起了職工浴池,每周開放六天,職工家屬也可以到澡堂子洗澡,惟獨周六為女職工洗澡日。說道女職工洗澡日,不禁讓人想起一件趣事。
話說有一個姓李的師傅,因年紀大了,到廠收發室打更。打更每天都要上班,沒有星期禮拜,時間一久,對周日、周末的概念就有些淡漠。有一天,李師傅見廠里的人走的差不多了,就托付一起打更的照看一會,自己拎著毛巾肥皂去洗澡。走到浴室外間,急匆匆脫了個精光,穿著木拖鞋便進了浴室。浴室里蒸汽氤氳,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東西,這時,他仿佛聽到浴室里有聲音,像是有人洗澡。他正在愣神,只聽水池子里有人說話:“李師傅洗澡來了?”李師傅嚇了一大跳,忽地想起,今天大概是周六。慌亂中,也不知衣服是怎么穿上的。
在浴池里洗澡的果然是一位女同志。此人是市里國營企業的第一位女干部,四十幾歲年紀。她和李師傅在一個廠里工作多年,彼此都很了解。她知道李師傅是記錯了日子,否則,一貫老實巴交的李師傅,借他個膽子,也不敢在女職工洗澡日闖入女浴室。反倒是李師傅,聽到浴室里傳出女人的聲音,嚇得張徨失措,落荒而逃。據說,李師傅臨出門,這位女干部還調侃一句:“李師傅,怎么不洗了?”
三十多年前,因為經濟條件差,住房困難,根本談不上衛生設施。加上家里人口多,那時十幾口之家多的是,人口少的也得五六口。好多人家都是三代同堂,幾乎所有人家都是兩代人同居一室,住南北大炕,甚至兩戶人家擠在一間屋子里也不罕見,這樣的境況,洗把臉都費勁,就別說洗澡了。說起來現在的年輕人難以相信,從解放前到改革開放前,通遼城里只有一家澡堂子,而且是私人產業,解放后歸為了國有,改為了國營。
說起澡堂子,那得要從通遼建鎮說起。通遼建鎮之初就有了南市場、北市場兩處飯館和妓院、劇場等場所。為適應需求,澡堂子也應運而生,這第一所澡堂子就建在了南市場。后來,有一個叫劉居正的在北市場附近又建了一座浴池,至此,通遼城里有了一南一北兩個澡堂子。
劉居正,有資料說是當年私建小街基的劉振廷的兒子。其身份為“退役日偽少將”。其實,建北澡堂子時,日寇還沒有侵占東北。但他在日偽時期成為漢奸卻是事實。通遼歷史資料里,對劉居正是有所記載的:1945年8月15日,通遼成立“地方治安維持會”,日偽少將劉居正任會長;10月15日,成立通遼縣臨時政府,劉居正為代理縣長。1946年3月20日至24日,中共通遼中心縣委提議召開了臨時參議會,其中,議程里有“清算漢奸劉居正、沈子奇等人罪行”。
劉居正不僅修建澡堂子,還在北市場開妓院,并建過一座磚木結構的戲樓,后在一場大火中被燒毀。此人解放后被鎮壓。這些雖為題外話,但隨著劉居正的被鎮壓,他建的澡堂子也隨之停業散攤。通遼城從此就僅剩下一個澡堂子了。
在當時,澡堂子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夠經常光顧的地方。一般人不趕上特殊情況都不會去澡堂子洗澡,因為去洗一次澡要花三毛錢呢。三毛錢說起來不多,但那是當時一般工人一天工資的四分之一啊,是一家人一天足夠吃菜的錢。所以,要想洗澡,就去西遼河天然大浴池。夏季,每天都有很多人泡在西遼河里,人們撲騰一陣,連消暑帶洗澡,一舉兩得。講究點兒的回來的路上,找一口水井,用柳罐斗提上沁涼的井水從頭到腳澆上一遍,會更舒適。但美中不足的是這個天然浴池有時令性,只有夏天才行,春秋水太涼,冬季就成了冰場。女人要想洗澡就更加困難,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躲在角落處偷偷擦一擦。
那些賣苦力的每天都弄得一身汗、一身泥,但大多數人也只有到過年時,才會去一次澡堂子。
澡堂子里有專人招呼顧客,他們是澡堂子里為數不多算穿衣服的人。他們有一個習慣,喜歡在頭上扎一條白毛巾,毛巾扎法既不同于山東人,也不同于“偷地雷”的河北人,他們是把毛巾縷起來,從腦后攏過來,在腦門上系一個扣,在當時這也成了他們的行業標志。
進了澡堂子,墻上寫著“貴重物品交柜保管”字樣。手表、金錢等不交柜,損失自負;大廳里有幾排兩兩相對的床,床頭有一只小柜。
澡堂子最初沒有淋浴,只有一大一小兩個貼著瓷磚的池子,大池子里水溫稍低。那時洗澡,講究“泡”。坐在熱水池子里,一泡就是老半天,直到渾身燙得發紅才算過癮。澡堂子的好處之一就是,凡是進了屋,都脫得一絲不掛,沒有了貴賤之分,地位之別。百姓官員、警察小偷、掌柜伙計、車夫兵痞,一律“赤誠相見”,毫不掩飾。去洗澡的人澡堂子會給每人發一條浴巾,有的人松松垮垮地圍在腰上,擋住“要害”,也有人不用,泡夠了,到大廳里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覺。也有人要上一壺“葉子”,半斤果子,連吃帶喝,還有就在澡堂子里下棋的,休閑自在夠了,然后回去再泡。
雖然說大家都光著身子,身份平等,但是從膚色上還是大致能看出差異:有渾身上下皮膚細白的,有兩頭黑中間白的。從皮膚上就能大概猜得出他們的職業,白嫩的,不是商店掌柜伙計,也是機關文員;而那些一身腱子肉,除了被短褲常年遮掩的部位以外通體黝黑的,自然是干力氣活的。
有了澡堂子,就有了常客。一些有閑錢又有閑工夫的人往往吃飽了早飯,就早早去澡堂子,因為這時的水干凈。澡堂子里的水往往從早到晚一天不換,如果去得晚了,水就像泥漿一樣,有人調侃說,水稠得像 子一樣,連腳都伸不進去。
澡堂子還是唱歌的好地方。有人專門喜歡在澡堂子里唱歌、唱戲,時人稱“澡堂子唱手”。澡堂子里不論地面、墻壁、水池子,除了水泥就是瓷磚,所以攏音,猛地一嗓子,經反射后的聲音分外好聽。另外,或許是澡堂子里的蒸汽對嗓子也有幫助,好多人一到澡堂子,嗓子就“開了”,感覺唱出的聲音比在外面唱得好聽多了。因此,有些人想唱歌也會去澡堂子洗澡。
要說那時的澡堂子設施雖然沒有現在的高檔浴池好,但服務設施和質量卻不比如今差。不但有專門搓澡的師傅,他們還統一著裝,半袖淺藍色上衣,配白色短褲。那時當搓澡師需要專門拜師學藝。好的搓澡師傅講究的是手法,一條毛巾纏在手上,從臉開始,額頭、臉頰、耳根、脖子,依次往下,一直到腳。不同的皮膚用不同的力度,毛巾搓在身上,剛柔相濟,擦得皮膚微紅,渾身舒坦。搓澡師傅還擅長按摩推拿,在各關節和穴道上敲擊一遍,能擊打出花點,節奏鮮明,富有樂感。最后是抻指頭,把顧客的十個手指依次抻一遍,每抻一下,“啪”地一聲脆響。一套搓、敲、抻、按下來,保你遍體的骨頭松散,睡意朦朧。
澡堂子里還專設一間小屋,是給剃頭師傅預備的。很多人在澡堂子里洗完澡順便就剃頭,在這兒剃頭有一樣好處,就是省去洗頭這一層。
俗話說,“飽了不剃頭,餓了不洗澡”。剃頭難免要低頭彎腰,剛剛吃飽了去剃頭,肚子窩著不舒服;而洗澡消耗體力,餓了洗澡,容易頭暈眼花。可澡堂子里卻真的把這兩個行當合在了一起。可有一樣,凡是要剃頭的,都是先洗澡,等肚子里的東西消化得差不多了才去剃頭。
澡堂子里除了洗澡、剃頭還有修腳師傅。洗澡后腳干凈,沒有臭味,同時,腳底也泡軟了,好干活。那時的鞋襪遠不如現在的舒服合腳,加上“扛大個”的、推膠車的、出力氣的人走路多,又負重,很容易得腳疾,最多的是長雞眼、腳趾甲畸形。江湖上也有專治雞眼的,地上鋪一塊白布,用墨水畫著腳上的各種疾病,為的是做廣告,有來修腳的,就在當街把腳搬起來,放在自己的大腿上,用小尖刀往外摳雞眼、修腳趾甲,鮮血淋漓,看著 人。因此,更多的人愿意到澡堂子修腳,是因為既衛生又安全。
修腳師傅與理發匠、澡堂師傅、櫥子、跑堂等都屬于服務行業。按舊社會的說法叫“伺候人的”,都屬于“下九流”之列。惟獨修腳師傅卻是上九流。有一種說法,說是其他屬于下九流的“伺候人”時都要站著,修腳師傅則不然,即便是給王侯將相,甚至皇上修腳,也得坐著。你想,能和皇上“平起平坐”,地位能低得了嗎?
按舊俗,各行各業都要有祖師,澡堂子也不例外。各地澡堂子供奉的祖師不盡相同,有的供葛洪,就是自號抱樸子的煉丹家、醫藥學家。老通遼澡堂子供奉的祖師爺是姜子牙。老東北門有一戶澡堂世家,每逢春節,都要在西房山豎起一根旗桿,旗桿上有刁斗,下有神龕,點著香燭。姜子牙是封神榜上的人物,封神時把所有的神都封完了,卻忘了自己,只得將自己封在旗桿之下。至于他如何成為澡堂業的祖師不得而知。
解放后,澡堂子改成了通遼“國營浴池”,地點就在“圈樓”步行街西南角,上世紀八十年代市政府改造露天市場,建起“圈樓”及幾幢樓房,惟獨浴池沒有動。一座破舊二層小樓在那里堅持了多年。
隨著城里人口不斷增多,國營企業職工每人每月發一張澡票。同時,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,加上政府號召大搞“愛國衛生運動”,洗澡的人成倍增加,浴池里每天人滿為患,但浴池卻沒有因此增加,依舊是一花獨秀,一直到近三十年才遍地開花。
不過,上個世紀六十年代,市里較大的企業,如農機廠等已建起了職工浴池,每周開放六天,職工家屬也可以到澡堂子洗澡,惟獨周六為女職工洗澡日。說道女職工洗澡日,不禁讓人想起一件趣事。
話說有一個姓李的師傅,因年紀大了,到廠收發室打更。打更每天都要上班,沒有星期禮拜,時間一久,對周日、周末的概念就有些淡漠。有一天,李師傅見廠里的人走的差不多了,就托付一起打更的照看一會,自己拎著毛巾肥皂去洗澡。走到浴室外間,急匆匆脫了個精光,穿著木拖鞋便進了浴室。浴室里蒸汽氤氳,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東西,這時,他仿佛聽到浴室里有聲音,像是有人洗澡。他正在愣神,只聽水池子里有人說話:“李師傅洗澡來了?”李師傅嚇了一大跳,忽地想起,今天大概是周六。慌亂中,也不知衣服是怎么穿上的。
在浴池里洗澡的果然是一位女同志。此人是市里國營企業的第一位女干部,四十幾歲年紀。她和李師傅在一個廠里工作多年,彼此都很了解。她知道李師傅是記錯了日子,否則,一貫老實巴交的李師傅,借他個膽子,也不敢在女職工洗澡日闖入女浴室。反倒是李師傅,聽到浴室里傳出女人的聲音,嚇得張徨失措,落荒而逃。據說,李師傅臨出門,這位女干部還調侃一句:“李師傅,怎么不洗了?”
贊
已有0人點贊
找對象

-
上一條:老通遼回眸之十五——遠去的童趣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