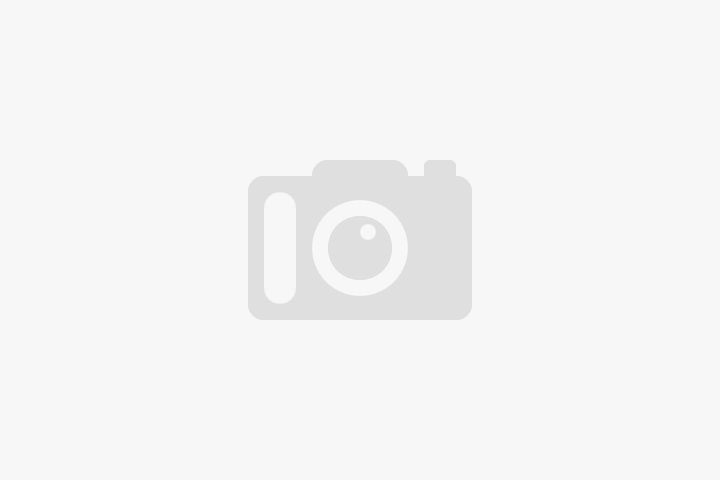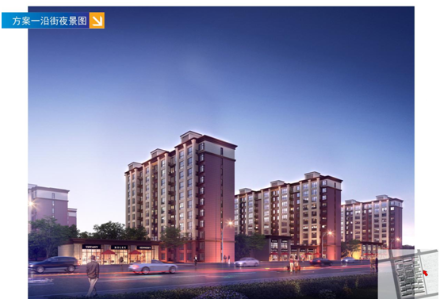正在閱讀:老通遼回眸之十—和十二————老通遼的胡同和陽溝
分享文章
微信掃一掃
參與評論
0

信息未審核或下架中,當前頁面為預覽效果,僅管理員可見
老通遼回眸之十—和十二————老通遼的胡同和陽溝
轉載
![]() mingyu于 2016/05/20 15:42:28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9028 閱讀
0 評論
28 點贊
mingyu于 2016/05/20 15:42:28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9028 閱讀
0 評論
28 點贊
胡同,南方叫巷、里弄、弄堂。是從蒙古語“忽洞格”——井,轉化過來的。元建大都時,因井而有人家,逐漸將蒙語“忽洞格”井轉化為胡同。北京、沈陽胡同都不少。
最初建通遼,劃井字街道,橫平豎直,在每條街道中再分胡同,胡同均為南北走向,每條街五條胡同。既方便出入,又便于管理。偽滿時將居民區劃“閭”,大約每兩條胡同為一閭,設閭長一人。解放后改閭為居委會下的居民小組,閭長改為組長。
胡同寬約五六米,可以走大車,胡同兩旁就是人家。雖然住戶大多是正房,坐南朝北,但院門大都朝著胡同。當時,很少有人家建高高的院墻,多采用秫秸夾杖子(柵欄)或齊胸高的土墻;有條件的人家,則用“板皮”釘柵欄。早晨起來,隔著院墻,兩家人親親熱熱打招呼;誰家改善生活包餃子,隔著墻頭給鄰居送過一碗;趕上燉魚沒有醋,隔著墻頭喊一聲,“嫂子,趕緊把醋瓶子遞給我”!住胡同的好處,就是界壁臨右如同一家。隨著城市不斷拆遷改造,小胡同已經近乎絕跡,小胡同留給人們的溫馨也漸行漸遠。
通遼城里到底有多少胡同,沒見過統計數字。這些遍布全城的胡同有名字的少,沒有名字得多。有名字的胡同幾乎都在繁華熱鬧的商業區,也或多多少少有點故事。
通遼城里最有名的,莫過于南市場、北市場兩個胡同。
北市場貫通南大街與中大街,即現明仁大街與中心大街兩條最繁華的鬧市區。開埠以來,這里就是城里的商業中心,南大街銀號、貨棧、醬園、藥鋪林立;中大街的布匹綢緞莊、估衣鋪以及城里唯一一座“洋樓”都成了吸引人的場所。北市場胡同只有二百米長、寬不足六七米,但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,加上一家挨一家的飯館、茶館、說書場、戲樓,以及隱藏在胡同兩側的妓院,使這里成了達官貴人,富商大賈、警察兵痞、平頭百姓、市井無賴購物、逛街最佳去處,結黨營私、揮金買笑的溫柔之鄉。特別是1922年通遼有了電燈之后,每到夜晚,胡同里燈火通明,飯館里飄出酒香肉香,說書館里傳出弦鼓之聲,大戲樓里從各地請來的名角,輪番上演著連臺大戲。通遼城南原有一座澡堂子,隨著北市場的興旺,由劉居正投資在北市場北口又建了一座澡堂子,從此有了一南一北兩個澡堂子。這座澡堂子位于現永清大街北側一條胡同里,通遼城里這條長220米的胡同就有了名字——北澡堂子胡同。劉居正不僅修澡堂子,還在北市場里建了一座戲樓,樓高二層,外砌青磚墻,內有木樓梯、地板,設包廂、雅座。后來在一場無名大火中焚毀。
南市場堪與北市場相媲美。這條胡同為東西走向,東起現和平路,西至新開胡同,在現向陽大街與科爾沁大街之間,全長250米,這里不僅有南戲樓、南澡堂子和飯館、皮影院、說書場,最多的還要數“窯子”,通遼城著名的妓院大都集中在這一帶,據資料記載,通遼城內的妓院不僅“起步早”,而且數量多。起步早,是說在通遼建鎮第二年就有了妓院,妓院最“昌盛”時,二等妓院十二家,一般妓院一百多家,從業妓女五百多人。在各行業中,妓院穩居榜首,占全城行業中八分之一,全城每百人中就有一點七個妓女。這還不包括暗娼和野妓。其中,最大的妓院“迎春院”有妓女30多名,“桂順堂”有妓女20多名。每到夜晚,嫖客、窯皮,站街的妓女、跑街的“茶壺”絡繹不絕。再加上偷偷摸摸賣春藥的,高聲大嗓賣瓜果梨桃、花生瓜子的,此起彼伏,直至深夜。這一“盛況”至1931年日本人占領通遼后,許多富商大賈紛紛逃跑,由于日本人壟斷經濟,造成經濟蕭條,民不聊生,妓院業逐漸有所收斂,卻增加了“新坤家”、“料理屋”之類日本妓院,新來了20多位身穿和服、趿拉著木屐的日本妓女。
新開胡同,全長215米,寬5米,南起南順城大街(向陽大街)北到南大街(明仁大街),1930年前后形成。新開胡同南端就是南市場,出北口往東不遠就是北市場,因此,這條胡同集中了多家飯館,一家名叫南海興的飯館是當時全城最有名的飯莊。
敖包胡同。敖包胡同與真正的蒙古敖包沒有關系,而是兩個人的姓。解放后正式命名為振興胡同,南起中大街,北至北大街,南口正對著北市場胡同,北澡堂子胡同西。1922年商戶包連喜、敖巨峰二人分別在胡同東西兩側各建廂房一棟,房子式樣、高低一模一樣,且整個胡同內都是住戶,沒有買賣店鋪,老百姓取敖聚豐、包連喜二人姓氏合在一起,稱“敖包”胡同。
清真胡同。位于“小街基”西側,到1922年前后,這里先后有100余戶回民聚居,后來在現永清大街南側修建清真寺,這座清真寺坐西朝東,門前形成一條胡同。伊斯蘭教做禮拜等宗教儀式時,城內回民都匯聚在這里。胡同南起中心大街,北至永清大街,全長150米。
文久胡同。這是城里最短的一條胡同,東西走向,不足百米。東起交通路,西端就是老爺廟。因每年都要舉辦廟會,屆時人們從四方潮涌而來,這條位于居民區內的胡同里也是人滿為患。但以前沒有名字,日偽時期命名為“文久胡同”。
還有幾條歷史上曾經有過名字,多數是日偽時期命名,因使用時間不長,很快被人忘記。如“農情里”,字面上看就明顯不是老通遼胡同風格。這條胡同形成較早,大約在1922年前后修建南市場時就有。這條胡同南起現科爾沁大街,北至現向陽大街,與南市場胡同呈十字交叉。民國時期作為成立的農貿市場,小鬼子統治時期作為牲畜交易市場(后遷移到交通門外,現一中路西)。另外,在北城一帶還有實為胡同、寬敞胡同等。
建國后也曾命名一些胡同,如位于民主路與交通路之間、永清大街路南有一條“幼兒園胡同,是因為胡同北端正對著當時城里唯一的一所幼兒園而得名。新開胡同南端還有一條培育胡同,有人說,是因為正對著一中大門,取培育社會主義新人之意,也有人說這一代舊社會妓院集中,妓院解散后對妓女進行改造,因此有將其培育成新人之意。
解放后,曾對街道重新命名,同時,把胡同名稱制作成標牌,釘在胡同兩端的墻上。日偽統治時期所命名,帶有殖民色彩的胡同名稱一律改換成新名稱或予以取締。
有了街道房屋,相伴而生的就是“陽溝”。
陽溝,是城市排水工程,主要是除雨水。之所以叫陽溝而不叫陰溝,主要區別就在于陰溝是隱蔽的,而陽溝則是裸露在地上。要問通遼城內有多少條陽溝,只要數一數街道就知道。街道兩側,臨街房屋門前都有陽溝,縱橫交錯,布滿全城。
陽溝十分簡陋,就是在地面上挖一條不足一米寬的溝,人可以輕易從溝上邁過去。至于深度,則是因地制宜,以排水順暢為宜。陽溝需要過街,否則會影響行人車輛通行。當時過街涵洞也是因陋就簡,用較粗的柳木棚在上面,再厚厚地覆上一層土。
通遼風沙大,俗話說“一年兩季風,一季刮半年”。話是有些夸張,但也說明當時風沙肆虐的程度。大風一刮,就把許多沙土刮進陽溝里,再加上當時城內以土平房為主,每年都要用大量的堿土抹房子,每逢雨季,房頂上的土被沖下來,一部分被沖進陽溝里。臨街人家甚至把陽溝當成垃圾坑,臟水窖,把尿盆里的臟水。泔水和垃圾都倒進陽溝。因此,每年春季都要組織人挖陽溝。陽溝里的土挖出來按說應該及時運走,但臨街機關單位和商店門前還好,一些居民的門前就慘了,總有很多土被甩到房屋一側。以至于房根底下年年增高。
在通遼城里,還真有兩條“講究”的陽溝,就在“敖包胡同”里。或許是建房時敖聚豐、包連喜兩人商量好了,不僅兩家的房子蓋得一模一樣,還在離墻根半米遠的地方各修了一條陽溝,與眾不同的是,這兩條陽溝很窄,不足一尺,深度也在一尺左右,并且用青磚砌溝底和溝壁,臨街的人家在門前放上一塊木板,便于行走。
通遼城內最大的一條陽溝位于霍林河大街南側,這是城內主排水道,城里的雨水都要通過這條陽溝排走。這條陽溝深兩米多,寬七八米。這條陽溝原本在老城壕南側,應該是修城壕取土時形成,后來幾乎被填平。
在這條陽溝西側靠近西遼河大堤附近,有一個連通西遼河的閘門。文革后期的一年夏天,不知什么原因,閘門被人打開,又正值西遼河來水。西遼河水順著閘門進了陽溝,因為這時城壕已經被挖平,水就順勢沖進城里,使現民大主校區南側一帶低洼處民房泡在水里。這一帶有好多陳舊的土平房,多年老鼠、潮蟲挖洞,墻根已經千瘡百孔,經水一泡,工夫不大,只見一間間小土房搖晃著化作一股煙塵,倒在水里。高玉良率人代表市里(現科區)前去視察災情,事后給受災戶重新蓋了新磚房。
城壕被鏟平后,北大溝被填平,又在原城壕北側重新開挖這條陽溝,作為城里排水主干道。八十年代中期在溝壁、溝底砌上石頭,但因經常積水,一段時間臭氣熏天,成了“龍須溝”。此后,先加了水泥蓋板,最后又改造成“帶狀公園”,在溝蓋板上填土,種上“爬山虎”,每到春季,一條綠色長龍 生機勃勃,十分養眼,成了市民休閑的好去處。不過,它也再不是“陽溝”,而成了地地道道的“陰溝”。
說起城里的陽溝,還有一段故事。
在通遼一中院內有一座水塘,是由當年“長記電燈廠”即后來的電廠挖的大坑改造而成。水塘里養了很多魚,一中的學生每天早晚都在水塘邊讀書學習,頗有一點“未名湖”的意思。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年,一天夜里下起大暴雨。越來愈大的雨水終于使水塘無法承受,池塘里的水決堤而出。那些久困在水塘里的魚們也爭相跳出龍門。雨一停,這些魚歸入了城內的陽溝。天亮后,人們發現陽溝里竟然有這么多大魚“從天而降”,急忙呼朋引伴,紛紛用臉盆、土籃子到陽溝里撈魚,人人收獲頗豐。那年頭,除非過年過節,平時很少能吃到魚,那一天,全城到處飄著燉魚的香味。
時至今日,城里的老陽溝都已絕跡,倒是最后形成的一條陽溝至今還好好的展現在路旁。這就是新興大街中段,和平路東側一條近百米的陽溝。1969年至1979年,當時的哲里木盟劃歸吉林省管轄,文革后期,吉林省派來“省宣隊”,隊員都是文革時被打倒或“靠邊站”的老干部,其中很多人被結合到盟。市革委會。加上盟里一些干部文革受沖擊,房屋被占,恢復工作后無房可住。于是,在老盟委后面蓋起兩棟二層住宅樓,這也是解放以來為領導干部修建的最為豪華的住宅。就在這兩棟樓房建成后,在其門前修了這條陽溝。陽溝不寬,僅一尺余,磚砌,外抹水泥,這也是當時城里最講究的陽溝。如今,作為城內僅余的一條陽溝,孑然存在。
最初建通遼,劃井字街道,橫平豎直,在每條街道中再分胡同,胡同均為南北走向,每條街五條胡同。既方便出入,又便于管理。偽滿時將居民區劃“閭”,大約每兩條胡同為一閭,設閭長一人。解放后改閭為居委會下的居民小組,閭長改為組長。
胡同寬約五六米,可以走大車,胡同兩旁就是人家。雖然住戶大多是正房,坐南朝北,但院門大都朝著胡同。當時,很少有人家建高高的院墻,多采用秫秸夾杖子(柵欄)或齊胸高的土墻;有條件的人家,則用“板皮”釘柵欄。早晨起來,隔著院墻,兩家人親親熱熱打招呼;誰家改善生活包餃子,隔著墻頭給鄰居送過一碗;趕上燉魚沒有醋,隔著墻頭喊一聲,“嫂子,趕緊把醋瓶子遞給我”!住胡同的好處,就是界壁臨右如同一家。隨著城市不斷拆遷改造,小胡同已經近乎絕跡,小胡同留給人們的溫馨也漸行漸遠。
通遼城里到底有多少胡同,沒見過統計數字。這些遍布全城的胡同有名字的少,沒有名字得多。有名字的胡同幾乎都在繁華熱鬧的商業區,也或多多少少有點故事。
通遼城里最有名的,莫過于南市場、北市場兩個胡同。
北市場貫通南大街與中大街,即現明仁大街與中心大街兩條最繁華的鬧市區。開埠以來,這里就是城里的商業中心,南大街銀號、貨棧、醬園、藥鋪林立;中大街的布匹綢緞莊、估衣鋪以及城里唯一一座“洋樓”都成了吸引人的場所。北市場胡同只有二百米長、寬不足六七米,但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,加上一家挨一家的飯館、茶館、說書場、戲樓,以及隱藏在胡同兩側的妓院,使這里成了達官貴人,富商大賈、警察兵痞、平頭百姓、市井無賴購物、逛街最佳去處,結黨營私、揮金買笑的溫柔之鄉。特別是1922年通遼有了電燈之后,每到夜晚,胡同里燈火通明,飯館里飄出酒香肉香,說書館里傳出弦鼓之聲,大戲樓里從各地請來的名角,輪番上演著連臺大戲。通遼城南原有一座澡堂子,隨著北市場的興旺,由劉居正投資在北市場北口又建了一座澡堂子,從此有了一南一北兩個澡堂子。這座澡堂子位于現永清大街北側一條胡同里,通遼城里這條長220米的胡同就有了名字——北澡堂子胡同。劉居正不僅修澡堂子,還在北市場里建了一座戲樓,樓高二層,外砌青磚墻,內有木樓梯、地板,設包廂、雅座。后來在一場無名大火中焚毀。
南市場堪與北市場相媲美。這條胡同為東西走向,東起現和平路,西至新開胡同,在現向陽大街與科爾沁大街之間,全長250米,這里不僅有南戲樓、南澡堂子和飯館、皮影院、說書場,最多的還要數“窯子”,通遼城著名的妓院大都集中在這一帶,據資料記載,通遼城內的妓院不僅“起步早”,而且數量多。起步早,是說在通遼建鎮第二年就有了妓院,妓院最“昌盛”時,二等妓院十二家,一般妓院一百多家,從業妓女五百多人。在各行業中,妓院穩居榜首,占全城行業中八分之一,全城每百人中就有一點七個妓女。這還不包括暗娼和野妓。其中,最大的妓院“迎春院”有妓女30多名,“桂順堂”有妓女20多名。每到夜晚,嫖客、窯皮,站街的妓女、跑街的“茶壺”絡繹不絕。再加上偷偷摸摸賣春藥的,高聲大嗓賣瓜果梨桃、花生瓜子的,此起彼伏,直至深夜。這一“盛況”至1931年日本人占領通遼后,許多富商大賈紛紛逃跑,由于日本人壟斷經濟,造成經濟蕭條,民不聊生,妓院業逐漸有所收斂,卻增加了“新坤家”、“料理屋”之類日本妓院,新來了20多位身穿和服、趿拉著木屐的日本妓女。
新開胡同,全長215米,寬5米,南起南順城大街(向陽大街)北到南大街(明仁大街),1930年前后形成。新開胡同南端就是南市場,出北口往東不遠就是北市場,因此,這條胡同集中了多家飯館,一家名叫南海興的飯館是當時全城最有名的飯莊。
敖包胡同。敖包胡同與真正的蒙古敖包沒有關系,而是兩個人的姓。解放后正式命名為振興胡同,南起中大街,北至北大街,南口正對著北市場胡同,北澡堂子胡同西。1922年商戶包連喜、敖巨峰二人分別在胡同東西兩側各建廂房一棟,房子式樣、高低一模一樣,且整個胡同內都是住戶,沒有買賣店鋪,老百姓取敖聚豐、包連喜二人姓氏合在一起,稱“敖包”胡同。
清真胡同。位于“小街基”西側,到1922年前后,這里先后有100余戶回民聚居,后來在現永清大街南側修建清真寺,這座清真寺坐西朝東,門前形成一條胡同。伊斯蘭教做禮拜等宗教儀式時,城內回民都匯聚在這里。胡同南起中心大街,北至永清大街,全長150米。
文久胡同。這是城里最短的一條胡同,東西走向,不足百米。東起交通路,西端就是老爺廟。因每年都要舉辦廟會,屆時人們從四方潮涌而來,這條位于居民區內的胡同里也是人滿為患。但以前沒有名字,日偽時期命名為“文久胡同”。
還有幾條歷史上曾經有過名字,多數是日偽時期命名,因使用時間不長,很快被人忘記。如“農情里”,字面上看就明顯不是老通遼胡同風格。這條胡同形成較早,大約在1922年前后修建南市場時就有。這條胡同南起現科爾沁大街,北至現向陽大街,與南市場胡同呈十字交叉。民國時期作為成立的農貿市場,小鬼子統治時期作為牲畜交易市場(后遷移到交通門外,現一中路西)。另外,在北城一帶還有實為胡同、寬敞胡同等。
建國后也曾命名一些胡同,如位于民主路與交通路之間、永清大街路南有一條“幼兒園胡同,是因為胡同北端正對著當時城里唯一的一所幼兒園而得名。新開胡同南端還有一條培育胡同,有人說,是因為正對著一中大門,取培育社會主義新人之意,也有人說這一代舊社會妓院集中,妓院解散后對妓女進行改造,因此有將其培育成新人之意。
解放后,曾對街道重新命名,同時,把胡同名稱制作成標牌,釘在胡同兩端的墻上。日偽統治時期所命名,帶有殖民色彩的胡同名稱一律改換成新名稱或予以取締。
有了街道房屋,相伴而生的就是“陽溝”。
陽溝,是城市排水工程,主要是除雨水。之所以叫陽溝而不叫陰溝,主要區別就在于陰溝是隱蔽的,而陽溝則是裸露在地上。要問通遼城內有多少條陽溝,只要數一數街道就知道。街道兩側,臨街房屋門前都有陽溝,縱橫交錯,布滿全城。
陽溝十分簡陋,就是在地面上挖一條不足一米寬的溝,人可以輕易從溝上邁過去。至于深度,則是因地制宜,以排水順暢為宜。陽溝需要過街,否則會影響行人車輛通行。當時過街涵洞也是因陋就簡,用較粗的柳木棚在上面,再厚厚地覆上一層土。
通遼風沙大,俗話說“一年兩季風,一季刮半年”。話是有些夸張,但也說明當時風沙肆虐的程度。大風一刮,就把許多沙土刮進陽溝里,再加上當時城內以土平房為主,每年都要用大量的堿土抹房子,每逢雨季,房頂上的土被沖下來,一部分被沖進陽溝里。臨街人家甚至把陽溝當成垃圾坑,臟水窖,把尿盆里的臟水。泔水和垃圾都倒進陽溝。因此,每年春季都要組織人挖陽溝。陽溝里的土挖出來按說應該及時運走,但臨街機關單位和商店門前還好,一些居民的門前就慘了,總有很多土被甩到房屋一側。以至于房根底下年年增高。
在通遼城里,還真有兩條“講究”的陽溝,就在“敖包胡同”里。或許是建房時敖聚豐、包連喜兩人商量好了,不僅兩家的房子蓋得一模一樣,還在離墻根半米遠的地方各修了一條陽溝,與眾不同的是,這兩條陽溝很窄,不足一尺,深度也在一尺左右,并且用青磚砌溝底和溝壁,臨街的人家在門前放上一塊木板,便于行走。
通遼城內最大的一條陽溝位于霍林河大街南側,這是城內主排水道,城里的雨水都要通過這條陽溝排走。這條陽溝深兩米多,寬七八米。這條陽溝原本在老城壕南側,應該是修城壕取土時形成,后來幾乎被填平。
在這條陽溝西側靠近西遼河大堤附近,有一個連通西遼河的閘門。文革后期的一年夏天,不知什么原因,閘門被人打開,又正值西遼河來水。西遼河水順著閘門進了陽溝,因為這時城壕已經被挖平,水就順勢沖進城里,使現民大主校區南側一帶低洼處民房泡在水里。這一帶有好多陳舊的土平房,多年老鼠、潮蟲挖洞,墻根已經千瘡百孔,經水一泡,工夫不大,只見一間間小土房搖晃著化作一股煙塵,倒在水里。高玉良率人代表市里(現科區)前去視察災情,事后給受災戶重新蓋了新磚房。
城壕被鏟平后,北大溝被填平,又在原城壕北側重新開挖這條陽溝,作為城里排水主干道。八十年代中期在溝壁、溝底砌上石頭,但因經常積水,一段時間臭氣熏天,成了“龍須溝”。此后,先加了水泥蓋板,最后又改造成“帶狀公園”,在溝蓋板上填土,種上“爬山虎”,每到春季,一條綠色長龍 生機勃勃,十分養眼,成了市民休閑的好去處。不過,它也再不是“陽溝”,而成了地地道道的“陰溝”。
說起城里的陽溝,還有一段故事。
在通遼一中院內有一座水塘,是由當年“長記電燈廠”即后來的電廠挖的大坑改造而成。水塘里養了很多魚,一中的學生每天早晚都在水塘邊讀書學習,頗有一點“未名湖”的意思。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年,一天夜里下起大暴雨。越來愈大的雨水終于使水塘無法承受,池塘里的水決堤而出。那些久困在水塘里的魚們也爭相跳出龍門。雨一停,這些魚歸入了城內的陽溝。天亮后,人們發現陽溝里竟然有這么多大魚“從天而降”,急忙呼朋引伴,紛紛用臉盆、土籃子到陽溝里撈魚,人人收獲頗豐。那年頭,除非過年過節,平時很少能吃到魚,那一天,全城到處飄著燉魚的香味。
時至今日,城里的老陽溝都已絕跡,倒是最后形成的一條陽溝至今還好好的展現在路旁。這就是新興大街中段,和平路東側一條近百米的陽溝。1969年至1979年,當時的哲里木盟劃歸吉林省管轄,文革后期,吉林省派來“省宣隊”,隊員都是文革時被打倒或“靠邊站”的老干部,其中很多人被結合到盟。市革委會。加上盟里一些干部文革受沖擊,房屋被占,恢復工作后無房可住。于是,在老盟委后面蓋起兩棟二層住宅樓,這也是解放以來為領導干部修建的最為豪華的住宅。就在這兩棟樓房建成后,在其門前修了這條陽溝。陽溝不寬,僅一尺余,磚砌,外抹水泥,這也是當時城里最講究的陽溝。如今,作為城內僅余的一條陽溝,孑然存在。
贊
已有0人點贊
新房
-

富源豪庭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華府在售
科左后旗 33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寶典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恒益·悅城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清華里在售
科左后旗 33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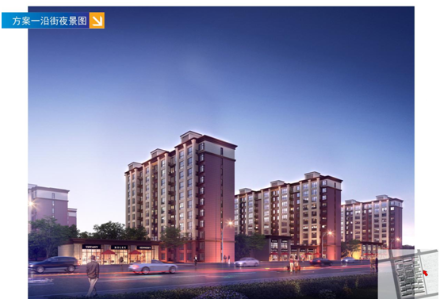
逸品藍山Ⅱ期在售
科左后旗 31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怡景嘉園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福園(理想家園B區)在售
科左后旗 30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郡府在售
科左后旗 3935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富源龍庭待售
科左后旗 409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博王·昊龍公館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甘旗卡商業廣場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
出租房
-

博王新村
科左后旗200㎡| 6室6廳 0元 面議 -

團結東區
科左后旗130㎡| 6室2廳 0元 面議 -
溫州商城二樓精品屋出租
科左后旗15㎡| 1室0廳 300元 面議 -

理想福園
科左后旗100㎡| 2室1廳 0元 面議 -
科左后旗200㎡| 6室1廳 0元 面議
-
 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
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 -
富源小區
科左后旗1000㎡| 20室2廳 0元 面議 -

一小學區房(2020)
科左后旗85㎡| 2室1廳 1000元 面議 -

街中心位置
科左后旗90㎡| 2室1廳 1125元 面議 -

綠源小區
科左后旗90㎡| 2室1廳 13000元 面議
二手房

-
上一條:老通遼回眸之十——小城叫賣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