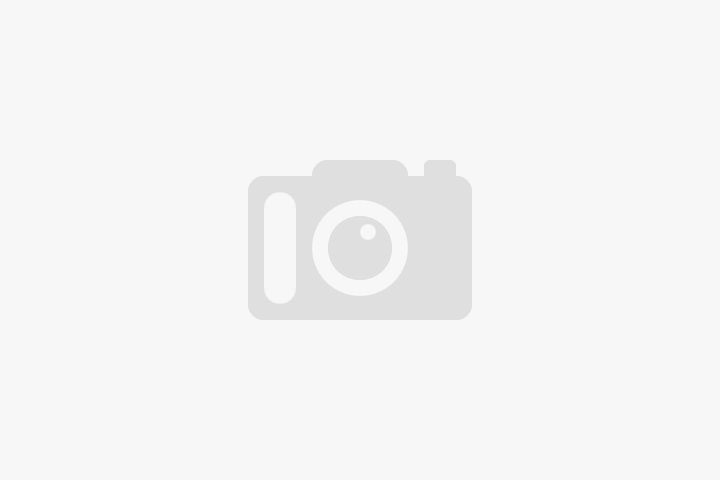正在閱讀:老通遼回眸之七·通遼曾有個二道壕
分享文章
微信掃一掃
參與評論
0

信息未審核或下架中,當前頁面為預覽效果,僅管理員可見
老通遼回眸之七·通遼曾有個二道壕
轉載
![]() mingyu于 2016/05/20 15:32:13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王玉濤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6694 閱讀
0 評論
26 點贊
mingyu于 2016/05/20 15:32:13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王玉濤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6694 閱讀
0 評論
26 點贊
老通遼四周建有城壕,西遼河岸上有防洪大堤。老通遼人,特別是城北一帶的人,習慣把護城壕稱作頭道壕,把西遼河大堤叫做三道壕。
那么,二道壕在哪呢?
二道壕建于1948年夏天。存在的時間也不長。因此,很多人把它遺忘了。
1948年夏天,西遼河水特別大,滾滾而來的洪峰夾著暴雨,接連不斷地沖擊著兩岸大堤。此時,通遼剛剛獲得解放,通遼人民擔負著支前、剿匪、土改等艱巨任務,這次洪水,無疑是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的一次嚴峻考驗。縣委主要領導組織群眾全力投入抗洪搶險第一線。
日為統治時期,只顧瘋狂掠奪財物,不管人民群眾的安危,西遼河大堤年久失修,加上日本投降后,通遼地區處于國共拉鋸時期,此時的西遼河大堤已經是千瘡百孔,險工險段隨處都是。在巨大的洪水壓力下,通遼城北的大堤終于不堪重負,洶涌的洪水沖出大堤,很快涌入通遼城。在干部群眾共同努力下,終于化險為夷,保住了通遼城。
此時,西遼河上游赤峰市正在下暴雨,預報還會有更大的洪峰到來。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,縣長王曉天決定:在護城壕和西遼河大堤之間再加筑一道防護壕。這道防護壕的位置為:西起西遼河西大壕原西遼河大橋北側,一直向東北方向,到雙井子西遼河大堤,全長十余華里。
當時,西遼河大堤決口處剛剛堵上,情況還不穩定,如果洪峰此時下來,隨時都有堤毀人亡的嚴重后果。特殊時期需要有特殊手段。王曉天縣長當即命令:民工要嚴守大堤,寸步不離。夜晚也不準回城。當時,確有一些人偷偷往城里溜。王曉天縣長當即命令秘書科長徐英,用二十響朝天鳴槍示警,同時,命令全體干部與民工同吃同住同勞動,認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。廣大干部群眾頂風冒雨,夜以繼日,苦干了七晝夜,一條長十華里的大堤橫亙在西遼河與通遼城之間,為通遼城加了一道保險。正因為它處于護城壕與西遼河大堤之間,從此,人們管它叫二道壕,西遼河大堤則成了三道壕。
由于西遼河大堤不斷加固,對通遼城的威脅日漸減小,二道壕存在的時間并不長。西側靠近河堤一段因栽種柳樹林被鏟平;和平路以東占用農田部分也逐漸被夷為平地。至解放后,只存在兩小段,其一,在現科區政府東側原龍王廟后身,也就是通遼公共墓地——祭古寺后面;另一段為通遼師范學院(現內蒙古民族大學主校區)北側。成為該校北墻的一部分。
當時二道壕選址時為何定在這個位置?說起來還有一段典故。
 在通遼建鎮以前,這里原有一道沙梁,其走向恰好與后來修建的二道壕走向一致。就在這到沙梁上,曾有一座蒙古人的敖包,位置在現科爾沁賓館門前。據說,這座敖包是科左中旗的中心點,被稱作科左中旗的“肚臍眼”,因此,這座敖包在科左中旗蒙古人眼里十分重要,經常舉行祭祀活動。這座敖包在日寇占領通遼時期還存在。當時,活動在通遼地區的抗日隊伍到處打擊侵略者,擊斃包括松井“司令”在內的很多敵寇。日本人為了悼念這些亡魂野鬼,在該處修建了一座“蒙古忠魂塔”,并在四周栽種了許多樹木。通遼解放后,推倒了忠魂塔,因四周樹木蓊郁,并且留有日本人丟下的一些體育器械,如訓練空軍飛行員用的大鐵環等,在沒有修建人民公園時,這里曾是周末群眾休息游玩之所。
在通遼建鎮以前,這里原有一道沙梁,其走向恰好與后來修建的二道壕走向一致。就在這到沙梁上,曾有一座蒙古人的敖包,位置在現科爾沁賓館門前。據說,這座敖包是科左中旗的中心點,被稱作科左中旗的“肚臍眼”,因此,這座敖包在科左中旗蒙古人眼里十分重要,經常舉行祭祀活動。這座敖包在日寇占領通遼時期還存在。當時,活動在通遼地區的抗日隊伍到處打擊侵略者,擊斃包括松井“司令”在內的很多敵寇。日本人為了悼念這些亡魂野鬼,在該處修建了一座“蒙古忠魂塔”,并在四周栽種了許多樹木。通遼解放后,推倒了忠魂塔,因四周樹木蓊郁,并且留有日本人丟下的一些體育器械,如訓練空軍飛行員用的大鐵環等,在沒有修建人民公園時,這里曾是周末群眾休息游玩之所。
此外,圍繞二道壕,城北還有幾處值得一說的地方。
沿著交通路出老北門,過一條土路,即現在的霍林河大街,路西有一片黑蒼蒼的樹林,樹木長得高大茂盛,楊柳樹、榆樹的樹稍上有很多老鴰窩,每當夕陽西下,成群結隊的老鴰遮天蔽日地在空中盤旋,使這里顯得陰森可怖。讓人感到恐怖的,還有一座小廟和廟后的一片墳地。
破廟就孤零零地蹲踞在這片樹林里,——通遼唯一的一座龍王廟。在以前的歷史資料中,對這座廟很少有記述,原因之一,就是這座廟修建年代不詳,而且建成不久就斷了煙火,沒有了道士,圍墻、配殿也相繼倒塌。再后來,龍王廟后身成了祭古寺,一個看墳的老頭就住在搖搖欲墜的破廟里。城里誰家死了人,都要送到祭古寺入土為安,所以,在這里時常可以看到披麻戴孝,抬著棺材的隊伍,哭叫聲、嗚咽的嗩吶聲伴隨著一串串紙錢飄散。看墳地的老頭事先挖好墳坑,等苦主來時收取一些費用。
在墳地西側不遠處還有一小片墳地,共有27座墳墓,與祭古寺里的墳墓不一樣的是,這幾座墳墓前都豎有石碑,刻寫著墓主人的名字,每到清明,城里機關單位及學校都要有組織地到此掃墓,這片墳墓就是1945年12月17日隱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奸細、土匪叛亂時犧牲的縣委書記徐永清、保安總隊隊長郭亞臣等烈士的墳墓。1959年9月15日,坐落在人民公園內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竣工,通遼市(科區)政府舉行揭幕典禮,盟、市領導及全市各界群眾代表參加典禮和骨灰安放儀式。遷移骨灰時,數千群眾自發來到徐永清等烈士墓前,在哀樂聲中將烈士骨灰護送至人民公園。
緊挨著徐永清烈士墳墓西側,有一塊很大的開闊地,空地上鋪著一條一條瀝青,像柏油馬路一樣。多年后,瀝青開裂,縫隙里長出一株株瘦弱的蒲公英、馬前子等生命力極強的植物,綻放著一朵朵藍色、黃色的小花。不要小看了這塊地方,這里正是日本侵略者當年修建的飛機場。
1931年,爆發了震驚中外的9·18事變,不久通遼淪陷。日寇將通遼當成向西進攻開魯、天山的橋頭堡,很快在通遼北門外修建飛機場。據《昭烏達蒙古史》記載,機場建成不久,臭名昭著的日寇頭目岡村寧次就乘飛機到達通遼,為向通遼以西的開魯、林西進攻作準備。
1945年8月,日寇宣布投降不久,通遼飛機場又迎來一位“大人物”,這位大人物竟是一位“皇上”,不過,此時他不但已經第二次宣布《退位詔書》,而且成了蘇聯紅軍押解下的戰俘。他,就是清遜帝、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愛新覺羅·溥儀。他被蘇軍押解著走下飛機后,乘坐吉普車到通遼城里住了一宿,第二天,又從這里上了飛機,被押解到蘇聯赤塔州。從此,這個日本侵略軍修建的飛機場隨著日寇的投降,結束了長達十三年的罪惡的使命。
順著交通路出老北門不遠,從“二道壕”北側,一直到“三道壕”根底下,馬路左側都是菜地,就在菜地的南邊有一口土井,這口土井的井口比一般的土井粗,井壁也是用柳條笆圍成,每到夏天,柳條笆上就生出一圈一圈的白蘑菇。經常有蛤蟆露出水面“呱呱”地叫。與眾不同的是,這口土井裝有一部水車,也是通遼唯一的一部水車。水車的部件除了一根伸到水里的“洋鐵管”和長長的鐵鏈子,其余都是用生鐵鑄造,井口的木架子上有一對傘齒輪,大的半徑五六十公分,鐵鏈子從洋鐵管子里穿出來,上面每隔一段有一塊圓形橡膠片,齒輪一轉,帶動鐵鏈子,就把井里的水抽出來。推動齒輪轉動的是一根很粗的木棍,正常使用的時候,應該使用毛驢拉。城里的人下鄉打柴火、剜野菜,走到這里都要停下來,趕上沒有毛驢車水,就自己推著水車,把水抽出來。如果是盛夏三伏,走得口干舌燥,喝上一口沁涼的井水,再洗上一把臉,頓時暑汗全消。按照通遼當時技術水平,還沒有能力生產這樣的東西,究竟是誰,在什么時間安裝的這部水車已不得而知。考慮到西北側不遠就是日本人在的時候修建的牲畜良種場,應該是他們安裝的。
那么,二道壕在哪呢?
二道壕建于1948年夏天。存在的時間也不長。因此,很多人把它遺忘了。
1948年夏天,西遼河水特別大,滾滾而來的洪峰夾著暴雨,接連不斷地沖擊著兩岸大堤。此時,通遼剛剛獲得解放,通遼人民擔負著支前、剿匪、土改等艱巨任務,這次洪水,無疑是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的一次嚴峻考驗。縣委主要領導組織群眾全力投入抗洪搶險第一線。
日為統治時期,只顧瘋狂掠奪財物,不管人民群眾的安危,西遼河大堤年久失修,加上日本投降后,通遼地區處于國共拉鋸時期,此時的西遼河大堤已經是千瘡百孔,險工險段隨處都是。在巨大的洪水壓力下,通遼城北的大堤終于不堪重負,洶涌的洪水沖出大堤,很快涌入通遼城。在干部群眾共同努力下,終于化險為夷,保住了通遼城。
此時,西遼河上游赤峰市正在下暴雨,預報還會有更大的洪峰到來。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,縣長王曉天決定:在護城壕和西遼河大堤之間再加筑一道防護壕。這道防護壕的位置為:西起西遼河西大壕原西遼河大橋北側,一直向東北方向,到雙井子西遼河大堤,全長十余華里。
當時,西遼河大堤決口處剛剛堵上,情況還不穩定,如果洪峰此時下來,隨時都有堤毀人亡的嚴重后果。特殊時期需要有特殊手段。王曉天縣長當即命令:民工要嚴守大堤,寸步不離。夜晚也不準回城。當時,確有一些人偷偷往城里溜。王曉天縣長當即命令秘書科長徐英,用二十響朝天鳴槍示警,同時,命令全體干部與民工同吃同住同勞動,認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。廣大干部群眾頂風冒雨,夜以繼日,苦干了七晝夜,一條長十華里的大堤橫亙在西遼河與通遼城之間,為通遼城加了一道保險。正因為它處于護城壕與西遼河大堤之間,從此,人們管它叫二道壕,西遼河大堤則成了三道壕。
由于西遼河大堤不斷加固,對通遼城的威脅日漸減小,二道壕存在的時間并不長。西側靠近河堤一段因栽種柳樹林被鏟平;和平路以東占用農田部分也逐漸被夷為平地。至解放后,只存在兩小段,其一,在現科區政府東側原龍王廟后身,也就是通遼公共墓地——祭古寺后面;另一段為通遼師范學院(現內蒙古民族大學主校區)北側。成為該校北墻的一部分。
當時二道壕選址時為何定在這個位置?說起來還有一段典故。

此外,圍繞二道壕,城北還有幾處值得一說的地方。
沿著交通路出老北門,過一條土路,即現在的霍林河大街,路西有一片黑蒼蒼的樹林,樹木長得高大茂盛,楊柳樹、榆樹的樹稍上有很多老鴰窩,每當夕陽西下,成群結隊的老鴰遮天蔽日地在空中盤旋,使這里顯得陰森可怖。讓人感到恐怖的,還有一座小廟和廟后的一片墳地。
破廟就孤零零地蹲踞在這片樹林里,——通遼唯一的一座龍王廟。在以前的歷史資料中,對這座廟很少有記述,原因之一,就是這座廟修建年代不詳,而且建成不久就斷了煙火,沒有了道士,圍墻、配殿也相繼倒塌。再后來,龍王廟后身成了祭古寺,一個看墳的老頭就住在搖搖欲墜的破廟里。城里誰家死了人,都要送到祭古寺入土為安,所以,在這里時常可以看到披麻戴孝,抬著棺材的隊伍,哭叫聲、嗚咽的嗩吶聲伴隨著一串串紙錢飄散。看墳地的老頭事先挖好墳坑,等苦主來時收取一些費用。
在墳地西側不遠處還有一小片墳地,共有27座墳墓,與祭古寺里的墳墓不一樣的是,這幾座墳墓前都豎有石碑,刻寫著墓主人的名字,每到清明,城里機關單位及學校都要有組織地到此掃墓,這片墳墓就是1945年12月17日隱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奸細、土匪叛亂時犧牲的縣委書記徐永清、保安總隊隊長郭亞臣等烈士的墳墓。1959年9月15日,坐落在人民公園內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竣工,通遼市(科區)政府舉行揭幕典禮,盟、市領導及全市各界群眾代表參加典禮和骨灰安放儀式。遷移骨灰時,數千群眾自發來到徐永清等烈士墓前,在哀樂聲中將烈士骨灰護送至人民公園。
緊挨著徐永清烈士墳墓西側,有一塊很大的開闊地,空地上鋪著一條一條瀝青,像柏油馬路一樣。多年后,瀝青開裂,縫隙里長出一株株瘦弱的蒲公英、馬前子等生命力極強的植物,綻放著一朵朵藍色、黃色的小花。不要小看了這塊地方,這里正是日本侵略者當年修建的飛機場。
1931年,爆發了震驚中外的9·18事變,不久通遼淪陷。日寇將通遼當成向西進攻開魯、天山的橋頭堡,很快在通遼北門外修建飛機場。據《昭烏達蒙古史》記載,機場建成不久,臭名昭著的日寇頭目岡村寧次就乘飛機到達通遼,為向通遼以西的開魯、林西進攻作準備。
1945年8月,日寇宣布投降不久,通遼飛機場又迎來一位“大人物”,這位大人物竟是一位“皇上”,不過,此時他不但已經第二次宣布《退位詔書》,而且成了蘇聯紅軍押解下的戰俘。他,就是清遜帝、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愛新覺羅·溥儀。他被蘇軍押解著走下飛機后,乘坐吉普車到通遼城里住了一宿,第二天,又從這里上了飛機,被押解到蘇聯赤塔州。從此,這個日本侵略軍修建的飛機場隨著日寇的投降,結束了長達十三年的罪惡的使命。
順著交通路出老北門不遠,從“二道壕”北側,一直到“三道壕”根底下,馬路左側都是菜地,就在菜地的南邊有一口土井,這口土井的井口比一般的土井粗,井壁也是用柳條笆圍成,每到夏天,柳條笆上就生出一圈一圈的白蘑菇。經常有蛤蟆露出水面“呱呱”地叫。與眾不同的是,這口土井裝有一部水車,也是通遼唯一的一部水車。水車的部件除了一根伸到水里的“洋鐵管”和長長的鐵鏈子,其余都是用生鐵鑄造,井口的木架子上有一對傘齒輪,大的半徑五六十公分,鐵鏈子從洋鐵管子里穿出來,上面每隔一段有一塊圓形橡膠片,齒輪一轉,帶動鐵鏈子,就把井里的水抽出來。推動齒輪轉動的是一根很粗的木棍,正常使用的時候,應該使用毛驢拉。城里的人下鄉打柴火、剜野菜,走到這里都要停下來,趕上沒有毛驢車水,就自己推著水車,把水抽出來。如果是盛夏三伏,走得口干舌燥,喝上一口沁涼的井水,再洗上一把臉,頓時暑汗全消。按照通遼當時技術水平,還沒有能力生產這樣的東西,究竟是誰,在什么時間安裝的這部水車已不得而知。考慮到西北側不遠就是日本人在的時候修建的牲畜良種場,應該是他們安裝的。
贊
已有0人點贊
找對象

-
上一條:老通遼回眸之六泱泱大水漫通遼
-
下一條:老通回眸遼之八--話說馬道尹府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