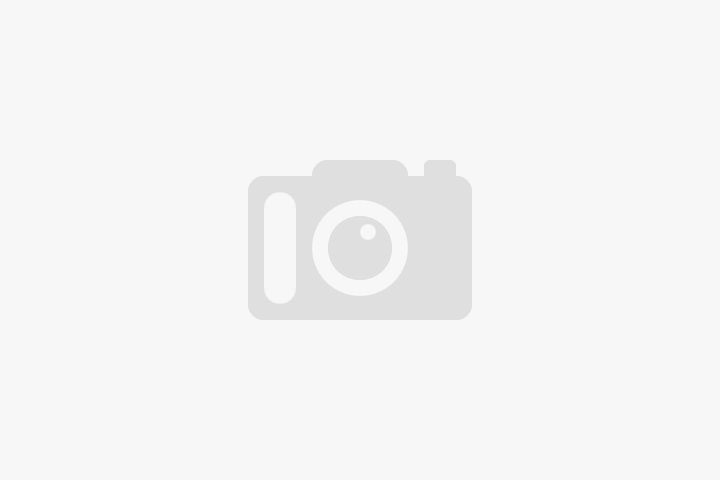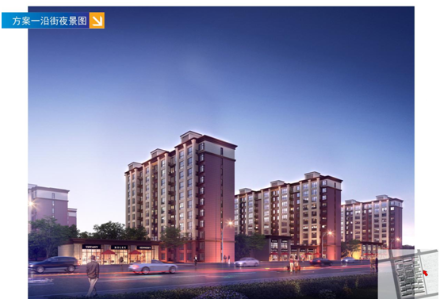正在閱讀:黑龍江呼麥第一人:阿古拉(科左后旗人)
分享文章
微信掃一掃
參與評論
0

信息未審核或下架中,當前頁面為預覽效果,僅管理員可見
黑龍江呼麥第一人:阿古拉(科左后旗人)
轉載
![]() 于 2014/08/22 09:57:50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11301 閱讀
0 評論
2 點贊
于 2014/08/22 09:57:50 發布
IP屬地:未知
來源:網絡
作者:瑪拉沁信息網
11301 閱讀
0 評論
2 點贊

資料圖
你有沒有聽說過“呼麥”這個詞?
這是蒙古語,是多聲部的意思。一個人在表演時,從嗓子里同時發出高、中、低多個聲音,奇吧。
你知道阿古拉這個人嗎?阿古拉是位蒙古族青年的名字,意為“青山”,現為杜爾伯特藝術團的馬頭琴演奏員。他是龍江呼麥第一人。
這位80后有著怎樣的藝術生涯?呼麥有著怎樣的魅力?近日,記者傾聽了阿古拉的講述。
快樂少年
阿古拉出生在科爾沁大草原的科左后旗。屯中有上千口人,是個大村。
他家養了不少馬,每天父親都要趕著馬群去放牧。到了牧場,馬兒撒著歡兒奔向草原深處。這時,父親把套馬桿往地上一戳,拔出腰間的竹笛,縱情吹奏。
阿古拉的母親雖然沒念過書,卻很聰明。只要是她聽過的歌,差不多全能模仿上來。親友相聚,或是屯中開會,阿古拉的母親總要出場演唱。
少年的阿古拉,放學之余總要去草原給父親幫忙,騎上駿馬追逐那飄揚的笛聲。
遼闊的草原綠茵如海,百花綻放,百鳥鳴唱,仰望藍天白云,阿古拉常常情不禁地唱兩句。
“啊哈伊勒……”阿古拉放開嗓子,歌聲隨即跟上了父親的笛聲,壓過了耳邊的風聲。
“太美了。”阿古拉如今還在陶醉,他說少年的快樂緣于一個快樂的家,更緣于寬廣的草原、湛藍的天空和蒙古族那粗獷豪邁的性情。
稀世技藝
上學后的阿古拉學習刻苦,門門課程都是優秀,并且精力永遠是那么旺盛。
他愛好運動,可是身體條件有限,踢足球太瘦,打籃球太矮,所以想當球類運動員成了奢望。
上音樂課就不同了,同一首歌,別人還沒學會,他已經用簡譜把這首歌記了下來。
一天晚上,阿古拉在收聽內蒙古人民廣播電臺播放的文藝節目。
突然,他聽到一個詞,叫“呼麥”伴唱。“呼麥?”他愣了一下,“這是啥樣的樂器?”
突然,收音機中傳出一陣如風吹哨起之音。這聲音由小變大,由弱變強,低、中、高三聲部清晰完美,造出山呼海嘯之境,讓阿古拉心馳神往。
“呼麥!呼麥是什么?”阿古拉趕緊問母親,母親沒說清。再問父親,父親說這是一種蒙古族獨有絕技。是由人的嗓子里發出的聲音。據說成吉思汗在位時,有個呼麥樂隊專為宮廷演奏,后來就失傳了。
“沒失傳,收音機里播放了……”阿古拉說。
“呼麥,呼麥到底是怎樣一種技法?就是找到天邊,我也要找出個究竟。”阿古拉下了決心。
為伊不悔
阿古拉在通遼民族大學藝術系錄取通知書到手的那一刻,喜憂參半。
“家庭困難,我是男子漢得先支撐這個家。”阿古拉跟母親說。
“男子漢志在四方,先要念書,念好書了才能撐起這個家。”父親勸著。
父親求親靠友拉了好幾萬元饑荒,把阿古拉送進了大學。
“您見過呼麥伴唱嗎?”第一堂基礎課一下來,阿古拉去問教授。
“見過,很古典的藝術。”教授肯定地回答。
“我能學學嗎?”阿古拉急切地問。“不好學啊。”教授說,阿古拉說自己不怕難,只要能學就行。
精誠所致,金石為開。教授以項目申報的方式,得到院方支持,一位呼麥表演師被請來教他們。
阿古拉被表演師如魔法般的表演深深吸引。
古老的呼麥有著無比的魔力。要掌握談何容易。第一次練習,阿古拉憋得紅頭漲臉。一天下來,他的嗓子腫得說不出話來,再看看同來的同學,走了一半。
“注意發聲部位,把握發聲氣息……”老師一邊示范,阿古拉一遍遍跟著練,再一天練下來,嗓子出血了。
“呼麥之聲是以喉頭憋出來的,很費嗓子。”阿古拉介紹說。
“練!入門啦。”老師肯定地鼓勵著。阿古拉順從而又痛苦地在血與聲中進步成長。
藝習百日功。三個多月的練習,阿古拉過了疼痛期,失音期,終于達到了初成期。
在一場學院藝術系專場演出中,阿古拉亮出絕活,全場轟動了。
后浪層層
2005年阿古拉大學畢業。他拖著沉重步子,回鄉待業了。
“杜爾伯特藝術團招馬頭琴手,你去試試。”一位同學向他提供了信息。他來到了杜爾伯特。住進每宿10元錢的小旅店。第二天去藝術團進行現場演奏,評委們一致的評價是:“很有藝術天賦。”讓他等一等。
等了兩個月,兜里的錢眼看沒了。午飯時,他去食堂見了藝術團團長王玉杰。
“團長,我實在沒有住店的錢了。”阿古拉眼睛盯著鞋尖,低著頭不好意思地對團長說。
“到團里宿舍住吧。”團長說。正規的考試終于來了,幾名應試者各展技藝。阿古拉的考核通過了,他急忙回家,親友們聽到喜訊,看見招聘合同十分高興,2006年春節一過,他上班了。
杜爾伯特,那遼闊的草原,讓他又找回了童年那段時光。杜爾伯特,雖然是他的第二故鄉,但這里的一草一木,讓他找到了歸宿感。
青春的活力,藝術的魅力,從舞臺飛揚,走進了人們的視線。
“藝術團來了個用嗓子發音的馬頭琴歌手。”一時間,阿古拉成了每次演出節目單外的“節目”。
“教教我的孩子。”求教之聲接踵而來。
“我是藝術團演奏員,再行教學之事合適嗎?”業余之時,他追問自己。
“藝術首先是民族的,隨著廣泛的傳播才成為大眾的,人類的藝術者只有去傳播,讓藝術長青,才是真正的人民藝術家。”老師的教悔,時時在他腦海回蕩。
2009年,杜爾伯特“激情之夏”進入藝術展時段。在阿古拉指導下的30名業余馬頭琴合奏者同臺獻藝,那萬馬奔騰之勢表現和抒發的何止是這個馬背上民族的豪邁。
5年來,在杜爾伯特縣泰康鎮的所有中小學校,都有馬頭琴手,最小者僅9歲,有10多位青年,因馬頭琴技藝術出眾,而考進了高等藝術院校。
阿古拉說:“呼麥于2009年已被確認為世界文化遺產,與馬頭琴相比,學習和教授難度很大。因為要過百日痛苦關,對于現在的青少年來說,傳授更難。作為民族樂手,傳授馬頭琴技藝是我人生的第一要務,也是傳藝初級期,第二步則是傳呼麥,我把它叫傳藝高級期,要歷經10年之苦教出一批呼麥手。有一天,當杜爾伯特的呼麥伴奏隊出現在大慶和中央電視臺的春晚,那才是我人生價值的展現。”
“讓呼麥走上央視春晚。”這不是夢想,這是一種傳播的弘揚。我們期待著。
推薦單位:杜爾伯特縣委宣傳部
記者 陳景波 卜憲九 文/攝
贊
已有0人點贊
新房
-

富源豪庭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華府在售
科左后旗 33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中興寶典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恒益·悅城在售
科左后旗 368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清華里在售
科左后旗 33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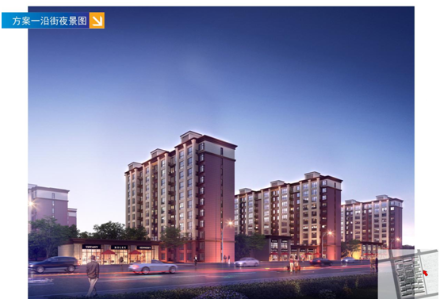
逸品藍山Ⅱ期在售
科左后旗 31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怡景嘉園在售
科左后旗 36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福園(理想家園B區)在售
科左后旗 30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理想郡府在售
科左后旗 3935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富源龍庭待售
科左后旗 409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博王·昊龍公館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 -

甘旗卡商業廣場在售
科左后旗 3500元/㎡ 價格待定
出租房
-

團結東區
科左后旗130㎡| 6室2廳 0元 面議 -
溫州商城二樓精品屋出租
科左后旗15㎡| 1室0廳 300元 面議 -

理想福園
科左后旗100㎡| 2室1廳 0元 面議 -
科左后旗200㎡| 6室1廳 0元 面議
-
 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2500㎡| 100室10廳 0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
科左后旗110㎡| 10室1廳 1元 面議 -
 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
科左后旗50㎡| 1室1廳 0元 面議 -
富源小區
科左后旗1000㎡| 20室2廳 0元 面議 -

博王御花苑
科左后旗90㎡| 2室1廳 0元 面議 -

金地鑫居
科左后旗69㎡| 2室1廳 1000元 面議 -

藍天下附近
科左后旗75㎡| 2室1廳 833元 面議 -

南區國稅小區
科左后旗90㎡| 3室1廳 11000元 面議
二手房

-
上一條:科爾沁草原的傳說——大青溝的由來
-
下一條:蒙古族禁忌文化之生活禁忌
0條評論
插入表情
承諾遵守文明發帖,國家相關法律法規 0/300
 微信公眾號
微信公眾號